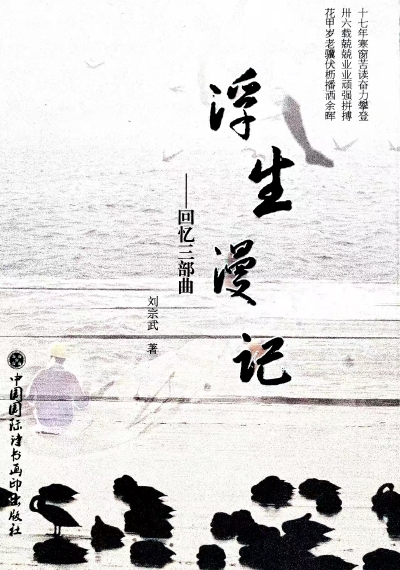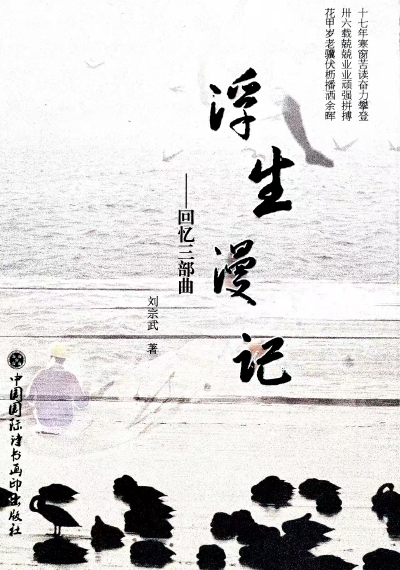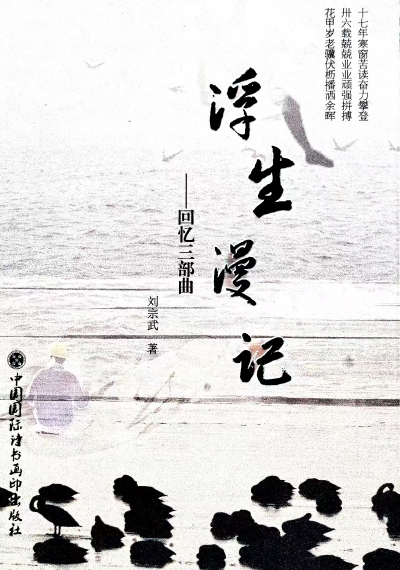人如其名劉胡來 違反政策生禍災
1947 年 11 月 17 日,農歷丁亥年十月初五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陳謝兵團 9 縱 26 旅 76 團在李鐘玄團長帶領下解放了夏店街。12 月 8 日,第 25 旅再次解 放臨汝之后,我的家鄉就應該算是解放了。正如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其他地方一 樣,武裝解放一片農村地區以后。都會成立農會,組織發動群眾,與反動地主封 建勢力作斗爭。
解放軍 76 團于 11 月 25 日攻克汝陽上店后便開赴前線,投入淮海戰役。 以毛萬年、周二云等為首的殘余土匪,又以夏店為中心活動起來,妄圖死灰復 燃,負隅頑抗。
1948 年農歷三月十四日夜里,解放軍 75 團改編成的臨汝縣獨 立團第二次解放了夏店。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發生的一些事情對我的家庭乃至我個人的一生產生了 重大而深刻的影響。
中原歷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上個世紀前半葉,也就是我出生之前的幾十 年,我的家鄉一帶更是戰火不斷,昨天,你打過來。今天,他打過去。明天,還不 知道誰又會再打過來。為了躲避戰火的“跑反”幾乎成了普通百姓的家常便飯。 作為身處遠離政治經濟中心,幾乎與世隔絕的山區,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普通 農民,幾乎沒有人愿意而且敢于在社會動亂的大背景下出頭。多數百姓的這種 心態,為一些膽大妄為者提供了渾水摸魚登臺表演的機會和舞臺。 1948 年年初,導師在其為新華社起草的《中原我軍占領南陽》電訊 稿中,曾經指出:“在去年下半年的一個極短時間內,我們在這一區域曾經過早 地執行分配土地的政策,犯了一些策略上的‘左’的錯誤。”導師提到的“這 一區域”就包括我的家鄉。
1947 年下半年,陳謝兵團配合劉鄧、陳粟大軍經略中原挺進豫西,迅速開 辟新的解放區。為充分發動群眾,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軍區指示在各新區普 遍地開展分浮財、分土地運動。正如當時的一些內部報告描述的那樣。此時的 中原解放區尚屬國共兩黨爭奪之地,俗稱“拉鋸區”,群眾的覺悟程度和干部的 準備情況也尚不具備土改條件。但是,“左傾”思想的蔓延使得中共基層組織“忽 視了群眾工作的艱苦性,把少數勇敢分子的行動誤認為是大多數群眾的行動。 把大軍進入后群眾一時的熱勁,誤認為是多數農民已經有了分配土地的覺悟和 要求”,提出“一手拿槍,一手分田,打到哪里,分到哪里”、“五天分浮財,半月分 土地”等激進口號。以致形成“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局面。許多村甚至達 到了“空其室而清其野”。釀成了亂打亂殺、亂沒收、亂破壞的“急性土改”。 在土改中,由于不恰當地過分堅持“貧雇路線”以“扎正根子”,有時“把少 數勇敢分子的意見作為實施政策的依據,把制定政策與修改政策的權限隨意交 給一個普通同志”。一些外來干部“對本地干部的作用認識不夠,也沒有精心 一意地發現正派的積極分子,大量地使他們成為村區干部。反而提拔了一批流 氓、壞人當干部。致使參加農會、貧農團的很多領導成員(勇敢分子)多為地痞 流氓,游手好閑之徒,土改‘果實’大多被他們裹去”。 就我現在的認識水平,我清醒地知道這種現象是部分的甚至是個別的,絕 不是那個時期中原解放區的主流。可是令人遺憾的是,這種個別現象偏偏讓我 的家鄉——劉窯村碰上了。 1947 年年底前后,劉窯村的劉胡來乘亂當上了劉窯村農民協會的主席,掌 握了全村的生殺予奪大權。劉胡來何許人也?真是人如其名,為了一己私利, 什么打家劫舍、殺人放火的勾當都敢任意“胡來”。 在洛臨公路開通之前,沿紫荊河蜿蜒而上、途徑劉窯村的一條小路是騾馬 馱客和步行客商往返于洛陽和駐馬店、南陽之間的“背大路”。有一次一個攜 款準備去漯河買牛的北鄉客商因天黑借宿他家過夜。不懷好意的劉胡來“熱 情招待”,待認定該客商確有銀錢在身之后,便在第二天假意帶路,把客商誘騙 至白沙溝偏僻處謀財害命。這些事在劉窯村幾乎是盡人皆知的“秘密”。 就是這么個主,當上農會主席后在村里為所欲為,干了許多違犯政策的 勾當。 首當其沖的就是不讓我家加入農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只知道我家 的家庭出身是“不在會”。一直到后來上了學,讀了書才知道,在農民家庭出身 劃分中,只有雇農、佃農、貧農、下中農、中農、富裕中農(上中農)、富農、地主幾 種,即便是加上小土地出租和資本家兼地主在一起也沒有“不在會”這種家庭 成分,才理解了所謂“不在會”,只是在解放初期沒有加入農民協會而已。其實, 在土改劃分成分時,根據人口和占有土地、房產、農具等資產,我家就是一個典 型的中農成分,連上中農也夠不上。然而,不僅我家的土地和 1946 年蓋的三間 新瓦房被分掉了,而且連我母親結婚時陪嫁的箱子和柜桌等也被當作浮財被分 掉了。還嚇得我大伯和父親雙雙不得不在外地東躲西藏以躲避批斗。而且我 大伯還莫名其妙地被戴上所謂“惡霸壞分子”的帽子,冤枉了好多年。而且因 為大伯“惡霸壞分子”的帽子,直接使我失去了一次寶貴的的招飛機會。 萬幸的是,正如導師所說,這種“急性土改”的左傾做法“隨即糾正了”。 1948 年進行了土改復查,我家的成分就是明明白白的“中農”,無論如何我家的 土地房屋和家產不應該被分掉。按照政策,我家被分掉的土地房屋應該原物歸 還。但是以劉胡來為首的村農會并沒有這樣做,而是把原本屬于我家的肥沃的、 離村子近、交通便利的諸如堂灣、小塘溝等地塊分給了別人,把一些貧瘠的、比 較偏遠、路道不好甚至是幾近荒蕪的、原不屬于我家的土地給了我家,令人費解 的是分給我家的土地面積比分走我家的土地面積還要略微大一些;把我家新蓋 的 3 間新瓦房和草屋頂的南屋一間臨街分給了別人,又把南院 4 間舊廈子和 1 間磨道(安裝有石磨的房子)分給我家。美其名曰,是為了“保護貧雇農的積極 性”。劉胡來們為了為他們的胡作非為尋求合法性,又給我大伯戴上了“惡霸 壞分子”的帽子。試想在那個“支部有殺人權”的混亂形勢下,連性命都無法 保障的情況下,找誰說理去? “善惡有報”是常理。中外古今,概莫能外。1962 年夏天,劉胡來一天晚上 在其門前的大石隔子上睡覺,第二天早晨發現他從大石隔子上一頭栽下,腦袋 被夾在兩塊石頭縫中間,死于非命。至于是他自己不小心從大堰上栽下去喪命, 還是突發腦梗心梗,抑或是被仇家所殺,始終無人得知,也許永遠是謎。這難道 不是一種報應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