廚房的燈,總在深夜亮著微光。她站在灶臺前,把涼透的排骨燉菜倒進鐵鍋,這是他最愛吃的菜,簇簇火苗舔著鍋底,像舔舐著她數不清的等待。
飯菜熱了第三遍時,門鎖終于傳來響動。他帶著酒氣和陌生的油煙味進門,瞥了眼餐桌,擺擺手對她說:“在外頭吃飽了,還是外面的飯菜好吃”,便歪在沙發上刷手機,看各式的美女。她看著刷手機的他,轉身默默把菜盛回白瓷碗,那碗沿印著他當年送的碎花,那時他對她說:“寶寶,以后咱們吃飯就在家里,還得用這么好看的碗才行”。那時她捧著碗望著他嗤嗤地笑,如今碗還在,笑意卻早被反復的溫熱熬成了涼。

某天,她又一次端起碗準備熱飯,指尖剛碰到碗沿,突然聽見“咔嗒”一聲脆響。哦,不是碗碎了,是她心里有什么東西,像經年的瓷,終于撐不住裂了縫。可她沒哭,也沒覺得痛,只蹲下身,看著地上散落的飯粒,突然想起很久前,她也是個怕燙的姑娘,連端熱湯都要墊著布,如今卻能徒手握著滾燙的鍋沿,連眉頭都不皺一下。
日子照舊,她還是每天買菜、做飯,機械麻木地一遍遍溫熱著飯菜。她心的裂縫越來越大,大到能裝下所有的失望,最后竟空了,像被掏空了米的陶罐,輕得發飄。那天她失神地望著窗外,光禿禿的枯樹枝椏戳在灰蒙蒙的天空里,可忽然間,她看見枝尖冒出一點嫩黃,是新芽,在最寒冷的日子里,竟悄悄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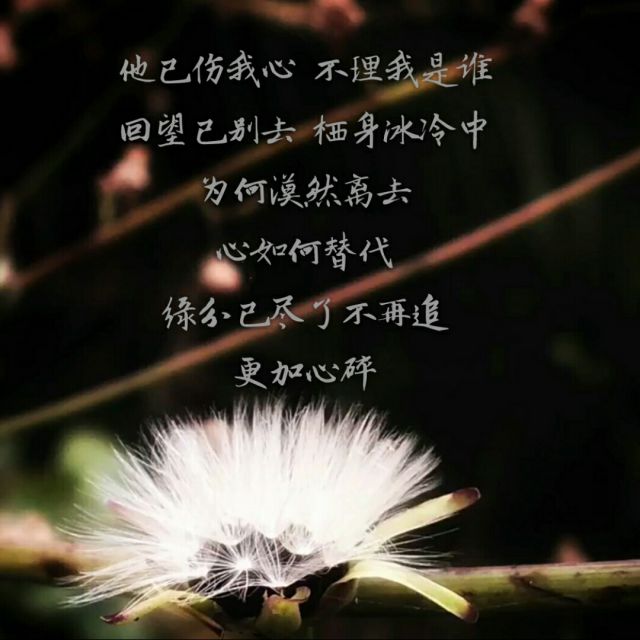
她轉身走到梳妝臺前,鏡子里的女人穿著洗得發白的圍裙,頭發隨意胡亂地挽著。她解下圍裙,慢慢梳開長發,烏黑的發絲垂在肩頭,像極了未出嫁時的模樣。目光掃過衣柜,角落里那件染了灰塵的綠色連衣裙靜靜躺著,布料還是當年的柔軟,顏色卻鮮得晃眼。她想起那時,她穿著這條裙子去公園,風一吹,裙擺飄得像小傘,那時的她,眼里有光,心里有夢,還沒學會圍著灶臺打轉。

原來,她早把自己弄丟了。那天下午,她收拾了行李箱,把綠色連衣裙疊得整整齊齊放進去。走到廚房,她拿起那套印著碎花的碗筷。他送給她的第一份禮物,也是她曾視若珍寶的東西,如今卻只覺得沉重。她打開垃圾桶,“哐當”一聲,碗筷落進去,碎瓷碰撞的聲音,竟比心里的裂縫愈合時,還要輕快。
她走了,沒留一句話,只在他的書桌上放了張離婚通知書。
一個月后,他在外面吃膩了重油重鹽的飯菜,突然想念家里的排骨燉菜,想念她遞過來時,碗沿擦得干干凈凈的溫度。他推開家門,迎接他的只有滿室清冷,餐桌空著,灶臺冷著,冰箱里連一顆菜都沒有。直到看見桌上的離婚通知書,他才慌了,手指捏著紙頁,抖得厲害,眼淚砸在“離婚”兩個字上,暈開一地傷痕。
后來的日子,他換了工作,不再徹夜不歸,卻總在路過菜市場時,想起她挑菜的模樣;看到別人家里亮著的廚房燈,想起曾經家里等他的微光。
又過了好幾年,他步履匆匆地路過一家旗袍店,櫥窗里的綠旗袍忽然抓住了他的目光。那顏色,像極了他記憶里的那條連衣裙。他忍不住駐足,看見店里的女人正對著鏡子淺笑,長發挽成優雅的發髻,綠色旗袍襯得她皮膚白皙,眼里的光,比當年更亮。

“是她!”他的心口像窒息般疼,沖進去拉住她的手腕,千言萬語堵在喉嚨口,最后只說出一句:“我很想你”。
女人轉過身,臉上沒有驚訝,也沒有波瀾,只是輕輕抽回手,淡然一笑:“先生,你認錯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