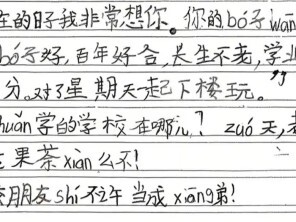信使是今晨抵達的。
沒有叩門,沒有通傳,只聽得蒼穹深處傳來極細微的帛裂之聲——那是天宇在拆閱一封自太古寄來的、純白色的信札。
信箋被風的手掌托著,一片,一片,又一片,開始悠悠地飄墜。起初,讓人疑心是哪個頑皮的云童,將貯藏在重樓深處的、去年未化的柳絮,一股腦兒傾了下來。但旋即你知道不是了,這分量,這氣勢,這覆蓋萬有的決心,只能是雪,也只能是中原的雪。
它落得那樣從容,那樣毋庸置疑。仿佛一個古老的諾言,在歷盡春的萌動、夏的喧囂、秋的沉淀之后,于萬物斂息的時刻,前來靜靜履約。謝道韞曾妙語“未若柳絮因風起”,然而眼前這雪,那比擬卻顯得過于輕巧了。它更似《詩經》里“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的“霏霏”,是綿長的、無邊的、帶著時間重量的思念,從古典的云端,一直下落到現代的原野。
這封信,最先被誦讀的,是神農山。
群峰是它默然聳立的第一個讀者。雪落在蒼黛的松針上,落在赤褐的崖壁上,落在蜿蜒若斷若續的山徑上。那嶙峋的、曾承載太多傳說與草藥的骨骼,漸漸被安撫得圓潤了,模糊了,仿佛一位峻肅的圣哲,在徹悟的瞬間,眉眼化作了慈悲。山靜默著,以千年的定力承受著這份潔白的覆蓋。偶爾有耐不住的寒鴉,“嘎”地一聲,從覆雪的巢中掙出,抖落一枝碎玉,那聲響便格外清冽,像一粒石子投入古潭,漾開的卻是無邊無際的岑寂。此刻,若王維在此,怕也要擱下畫筆,嘆一句“欲投人處宿,隔水問樵夫”了,因為這雪已將人跡擦去,將山河還給了洪荒初開時的本真。
繼而,信的內容,被黃河以它渾黃的、微瀾的軀體緩緩鋪展。
這條暴躁的巨龍,此刻也沉靜了,放緩了奔騰的節奏,仿佛在屏息閱讀一行行從天而降的素箋。雪片融入濁流,瞬間了無痕跡,像墨滴滲進宣紙,有一種獻身般的、溫柔的決絕。兩岸的田疇、村莊、阡陌,都被這統一的筆觸描摹成了一片朦朧而渾然的詩稿。極目望去,正如高駢登樓所見:“六出飛花入戶時,坐看青竹變瓊枝。如今好上高樓望,蓋盡人間惡路歧。”所有的崎嶇、分界與傷痕,都在這浩蕩的潔白下得到了暫時的平復與慰藉。天地如同一張剛剛鋪就的生宣,等待著,也凈化著。
而信中最溫暖的核心段落,一定是寫給那些麥田的。
那青青的、柔弱的麥苗,是大地面向天空書寫的最懇切的祈愿。如今,雪——這封回信——便以最豐厚的詞句回應了它們。一層,又一層,勻勻地、蓬松地,為它們覆上了銀白的錦被。這景象,樸素到讓任何華麗的辭藻都顯得冗余。農人披衣立于檐下,無須多言,眼底的安詳便是全部的注解。他們懂得這天地間最直白的訊息:“今冬麥蓋三層被,來年枕著饅頭睡。”在那雪被之下,冰涼的土壤里,正蜷臥著一個滾燙的、金黃色的夢。這夢如此沉實,讓人想起白居易體察萬物時的心境:“物以稀為貴,心因遠見幽。” 這覆蓋大地的尋常雪景,因關乎生存與希望,在農人心中,便貴重如金,幽遠如詩。
信也飄進了人家的院落。
黛瓦的坡度漸趨豐腴,木門的朱色在素白中顯得愈發溫存。窗內,燈火早早地亮了,將新剪的窗花“連年有余”的輪廓,暖暖地拓在雪幕上。屋內,爐火正紅,壺嘴噴吐著氤氳的白汽。這情境,天然便是一句邀約。不由得想起另一個欲雪的黃昏,香山居士那穿越千年的、溫潤的探問:“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風雪夜歸人,或是圍爐閑坐客,所求的,不過是這樣一份抵御洪荒的微光與溫情。雪,將世界關在門外,卻將人心拉得更近。
品讀至深,信箋漸薄。
萬物靜立,輪廓清晰如刻,卻又溫柔如夢。門前竹枝,不勝瓊瑤,“噗”的一聲,將滿懷的雪墜入大地,那聲音,空洞而圓滿。這無邊的寂靜,具有神啟般的力量。忽然便明了了《世說新語》里那份極致浪漫的“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這場大雪本身,便是全部的意義。它讓你在絕對的靜謐與純潔中,與自己照面,與天地共鳴。
及至午后,這封長信讀到了最后的篇章——融化。
那不是消逝,而是信中的每一個字句,化作了甘霖,開始向大地深處娓娓傾注。它滲入土壤的縫隙,去喚醒麥苗的根須;匯入黃河的脈動,去增添一股清流;也沁入村莊蘇醒的呼吸,成為晨炊煙霧里一縷看不見的滋潤。它履行了信的終極使命:將天上的訊息,轉化為地上的生長。這便是“瑞雪兆豐年”的全部奧秘,也是一切莊嚴宣告最終極的溫柔。
這一封自蒼穹寄往中原的雪信,以神農山為筆架,以黃河為鎮紙,以無垠田疇為信箋,以萬家燈火為句讀。它書寫的,是一場盛大的寂靜,一次深情的覆蓋,和一個關于蘇醒的、潔白無瑕的允諾。它告訴我們,最深的寒意里,包裹著最溫暖的生機;最靜的飄落,預告著最喧騰的春天。這,便是中原收到的,冬日里最隆重、最靜美、也最充滿希望的第一封來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