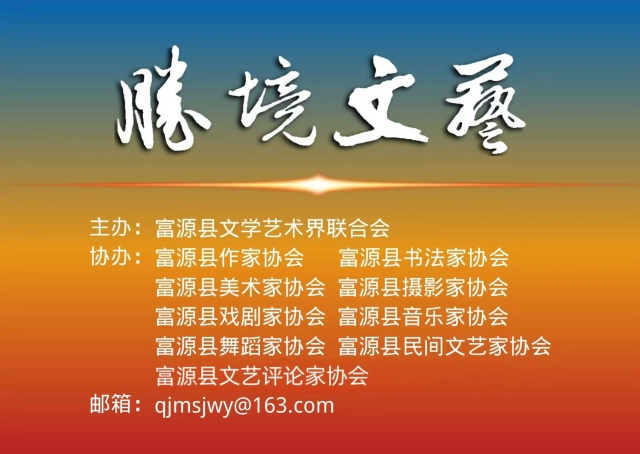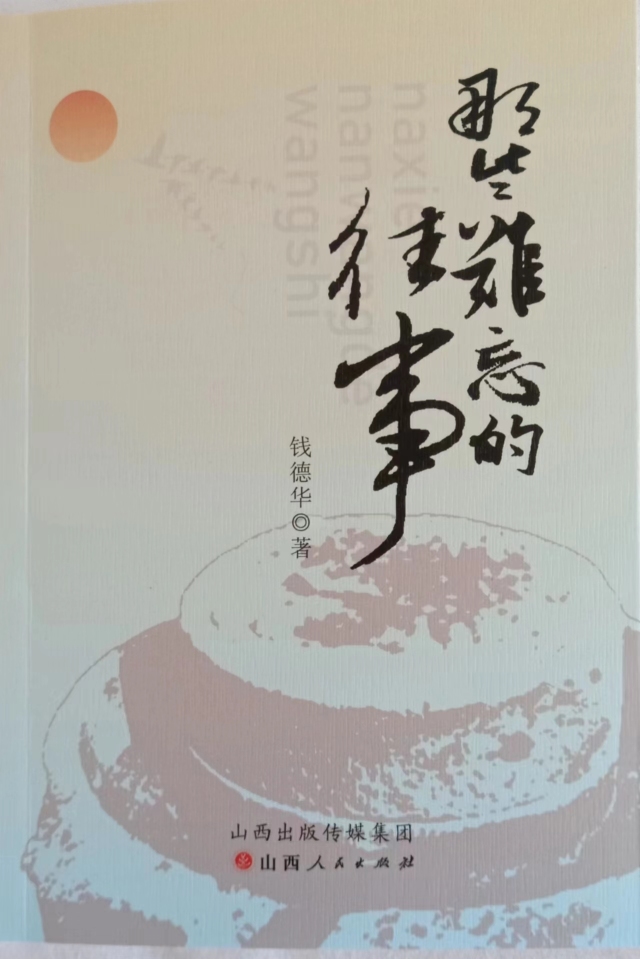
聽著窗外的鞭炮聲, 滿腔心酸。 今天是大年三十, 本該是團圓的日子, 爸媽卻永遠地缺席了。 每逢佳節倍思親, 除夕人不全, 心中思緒萬千。 唯愿爸媽在另一個世界里無病無災, 一切安好, 長眠九泉, 我們常思念!
這是 2024 年大年三十, 在抖音上看到外甥發的一段令人心酸的文字, 并配有我大姐的一組照片和一段傷感的音樂。
看著大姐歷盡滄桑但卻面帶微笑的照片, 聽著憂傷的音樂, 一字一句地讀著悲涼的文字, 對大姐過早地突然離世, 作為弟弟的我, 頓時潸然淚下, 多少往事, 隨即涌上心頭——
我的大姐和許多農村婦女一樣, 心地善良, 勤勞淳樸, 雖直言快語, 卻有嘴無心。 大姐每次說話時, 總是面帶微笑, 和藹可親, 具有中華民族傳統女性的優秀品質。
在我最早的記憶里, 我很小的時候, 父母要參加集體勞動掙工分, 因為大姐在兄弟姊妹七個中是大的, 排行第一, 我排行第四, 我上面是兩個哥哥 (后來, 母親又生了兩個妹妹和一個弟弟), 也就只有大姐背我了。 記得 20 世紀 60 年代初的一年, 正月下旬的一天, 大姐背著我, 和村中幾個小伙伴, 在我家的炭火上燒洋芋吃。 這天, 天氣很晴, 風也很大, 我家左邊石階路旁的一戶王姓人家, 不知什么原因, 房子旁邊我家堆的一堆松毛柴突然起火了。 由于風高物燥, 火苗越燒越旺, 很快就蔓延開來, 燒著了那家沒有用石頭砌山墻、 只用云柏枝攔著的瓦房。 大姐見外面起火, 她背著我跑出門去, 用松樹枝打火, 因火勢太大, 沒有撲滅。 隨后, 許多參加村中李貴德婚禮及幫忙的人聞訊趕來, 沒用多長時間, 大火就被撲滅了。 三間房子中, 靠邊這間房屋的一半被過了火, 燒得不太嚴重, 沒有坍塌, 只是柱子等木質材料燒煳了一層, 家里也沒有其他損失。 當天, 我父母在馬鞍山為集體鏟火土, 準備種大春洋芋的肥料, 傍晚回家后才知道火燒房子的事情。 那時我還小, 只是隱約記得, 當時有人說, 火是我大姐點燃了我家堆在那所房子邊的松毛柴才燒著房子的。 其實, 大姐根本就沒有點燃那堆松毛柴, 幾個小娃聚在我家燒洋芋吃, 只有我大姐大一點, 她大概 11 歲, 所以, 就冤枉給了我大姐。 我不知道當時父母罵了大姐沒有。 多年以后, 我聽大哥講了才知道, 火是我小叔家姑娘也就是我堂姐點燃的。 因為是我家堆的松毛柴在那里, 兩家都有責任, 被燒的這間房子, 由我家和我小叔家共同用新木料重新更換。
在 20 世紀 70 年代大集體時, 這間房子閑著, 中間用幾根木料簡單隔成柵欄, 一間分成兩半, 前半間沒有砌墻, 也沒有什么攔著, 四周敞開, 就是一個人走的過道。 后半間, 一直是我家借用作為關馬關牛關豬的畜圈, 在我讀書放假期間, 幾乎每天晚上, 都和我二哥在那間畜圈棚上用鍘刀鍘苞谷草喂牛馬。 幾年后, 我家蓋了兩間小耳房, 就沒有再借用了。 直到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 這家人才用石頭砌了山墻。 關于這件事, 大姐算是背了黑鍋。 所以, 時至今日, 雖然幾十年過去, 每每想起, 心情難平, 都為大姐打抱不平。
由于我們姊妹多, 和農村許多家庭一樣, 我家也很困難。 就連一張簡單的床鋪, 也不可能像現在一人睡一張。 大概是從我讀小學起到進入初中的幾年間, 都是大姐帶著我一起睡。 記得當年我和大姐睡的床鋪, 蓋的是一床舊棉被, 墊的是一床舊草席。 村里一個姓李的姑娘, 人長得很漂亮, 在我們二隊算是一枝花了。她的未婚夫家, 住在現在的鎮政府所在地, 是一戶大戶人家。 有一天晚上, 未婚夫來到她家, 她把自己的床讓給了未婚夫睡, 家里沒有多余的床, 就到我家來, 和我們擠在一起睡, 大姐睡一頭, 我和她睡另一頭。 因為她是客人, 大姐特地找了一條麻布口袋, 墊在客人身下的草席上。 那時, 家家戶戶條件都不好, 相互都不會嫌棄, 也才有了 “笑臟不笑破, 笑懶不笑貧” 的諺語。 后來, 我和二哥睡一張床的時候, 還墊過一張山羊皮。 對于如今不愁吃穿的年輕人來說, 那是不敢想象的事情。 我們那一代人, 吃過一些苦, 盡管現在有房有車, 吃穿用度寬裕, 但仍初心不改, 十分注重勤儉節約, 倍加珍視來之不易的幸福與美好! 也更希望年輕一代勤儉持家, 不鋪張、 不浪費, 讓艱苦奮斗精神得以繼承和發揚光大。 財富需要點滴積累, 奢侈浪費, 大手大腳, 難以聚財!
用秧草編織而成的草席, 也叫席子, 在那艱苦的歲月, 大部分人家都用它來鋪在床上墊睡, 熱天還涼爽, 到了冬天, 就十分冰涼, 特別是剛躺下時, 全身冷得直發抖, 每到這個季節, 夜晚最難熬。 但對于我來說, 好在有大姐, 她像母親一樣, 會把我的雙腳抱在她的懷里捂著, 讓我少挨一些凍。
盡管大姐對我這么好, 尚不懂事的我, 不知為什么, 還和大姐吵過一架, 罵了大姐幾句難聽的話。 雖然姐弟吵架是常事, 但在我心里, 卻一直是一道難以逾越的坎, 每次想起, 都很愧疚, 以至于在我參加工作后, 我回老家吃酒做客或看望父母, 只要遇到大姐, 都會給她一些錢, 有幾次, 在城里遇到外甥, 還托外甥帶點錢給大姐。 有一次, 借下鄉的機會, 我又買了一些米, 順便帶給大姐。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感恩大姐曾經對我的關懷和彌補對大姐的虧欠。
記得在我剛上初中那年, 星期六放假回家時, 考慮到第二天又要返校讀書, 大哥二哥又不在家, 他們被生產隊安排外出, 去拖竹上小煤窯和在老廠月六山對面一帶, 為八〇七地質勘探隊挖槽探 (一種探煤的勘探方式) 去了——大哥二哥為集體為家庭吃了很多苦, 可惜二哥 45 歲那年即 2002 年的正月間就突發疾病去世了。 因為在家里的勞力少, 父親就安排大姐帶著我, 利用月色, 去瓦廠溝砍集體分給我家喂牲口的苞谷草。 也許是父親和大姐一時記錯了月亮出來的時間, 吃過晚飯, 大姐就帶著我去砍苞谷草。 到了距離村子 1 公里遠的瓦廠溝上面羊毛土我家小墳堂邊時, 月亮還沒有出來, 但天已漸黑, 我有些害怕, 大姐便帶著我蹲在小墳堂旁邊的一塊大石頭邊。 四周一片漆黑, 伸手不見五指, 因是打霜季節, 氣溫很低, 穿得又單薄, 兩人只好依偎在一起, 等了一個多小時, 月亮才從對門山頂上冒出來。 那天晚上, 我們姐弟倆砍草砍了一個多小時, 幾臺長臺子地的苞谷草砍完后, 我們才回家。 在回家的路上, 不時聽到山野里傳來鳥獸的怪叫聲, 我因膽小, 大姐就叫我走在她的前頭。 其實, 當年大姐一個姑娘家, 她應該也很害怕, 她卻把害怕留給了自己。
也就是我進入初中那年, 大姐出嫁了。 大姐出嫁的頭兩天, 我在學校請了兩天假, 大概是 12 月份, 大姐出嫁那天, 看著大姐騎上娶親的喜馬, 就這樣和家人分開了, 情感上一時難以接受, 包括父母在內, 我們一家人都哭了, 我哭得更傷心, 從門外哭著跑到堂屋后面曾和大姐睡的那張床邊躲著哭, 難以抑制的如線淚水, 滴濕了衣襟——那是難以割舍的姐弟情啊!
大姐夫家在老廠鎮新堡村委會上普魯村, 我家所在的羊得補村隸屬者米村委會, 兩個村委會相鄰。 上普魯村距離我們村七八公里, 如走直路, 要經過名叫老井溝的一段路, 這段路就在上普魯村邊, 實際上這段路就是一座高山。 我們去大姐家時, 要從山頂下到山腳, 大姐回我們村時, 要從山腳爬到山頂, 壁立立的, 而且是像羊腸一樣彎彎曲曲的沙子小路, 非常難走, 特別是從山頂往下走時, 稍不小心就會滑倒, 甚至有滾下山坡的危險。大姐出嫁時, 沒有走老井溝這條路。 為了安全, 娶親隊伍從老井溝山頂處繞往新堡灑佐堡村旁的一條山路走了, 讓大姐能夠全程順利地騎馬到家。 在以后多年的日子里, 大姐每次回娘家羊得補村, 都從老井溝走, 直到后來修通公路, 再后來村里有了摩托車和跑運輸的面包車, 大姐偶爾來羊得補村吃酒做客時, 才不再走老井溝了, 這條大山上的小路也從此荒蕪了。
其實, 當年娶親的隊伍繞道走的那條路, 也不怎么好走, 因為海拔高低落差大, 同樣有些陡。 我原先不知道, 1986 年我在老廠區上工作時, 有一次我與副區長、 分管計劃生育工作的石維甫同志到新堡下鄉, 他有事先返回區上, 安排我一個人到上普魯村去開展幾天計劃生育工作, 他幾天后要到新堡樂額村開一次會, 我再與他會合, 然后一起返回區上。 于是, 我便從新堡村委會所在地的灑佐堡走大姐當年出嫁時曾走過的那段路去上普魯, 才知道那條路只是稍微平緩一些, 有土路, 有石板路, 但同樣高低不平, 還是很難走。
記得我在上普魯工作時, 吃住就在大姐家, 因為那時的計劃生育政策, 超生孩子要交超生費, 為了方便工作, 大姐夫專門為我騰了一只木箱子, 配了一把鎖, 還拿了一個帆布包包給我裝收取的超生費。 在六七天的時間里, 我一個人白天入戶做群眾思想工作, 晚上開群眾會, 反復宣傳政策, 工作倒也順利, 幾天時間就動員了六七戶超生戶主動交了超生費。
現在回想起來, 那時年紀輕輕的, 單獨一個人, 在村里開展當年被譽為比 “拉牛上樹還難” 的計劃生育工作, 并取得了一些成績, 受到了領導的表揚, 那是值得自豪的事情。 但我想, 如果不是當地村民看在大姐夫和大姐的面子上支持我的工作, 要取得如此成績, 應該是很難的。
在大姐家的幾天時間里, 我做的是公家的事, 卻辛苦了大姐。 大姐夫每天忙于農事, 家里早茶晚飯和其他家務活都是大姐操持。 那時, 剛剛包干到戶幾年, 大姐家也還有些困難, 但大姐還是盡量為我做些可口的飯菜——真是難為了大姐!
在大姐家, 我還得到了大姐夫送給我的他在當兵時從部隊帶回來的蘇聯作家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創作的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和馮德英創作的 《迎春花》 《苦菜花》 三部書。 這三本書, 成為我最早讀到的紅色革命小說, 對我后來的人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大姐既是一個幸福的人, 又是一個苦命之人。 說大姐幸福, 是因為她嫁了一個好人家、 好丈夫。 大姐夫說話輕聲細語, 和藹可親, 生怕語大聲高嚇著人。 他很有頭腦, 精于打算安排, 又能吃苦耐勞, 在村中人緣也很好, 我們一家人和許多認識他的人, 都很尊重他, 特別是我父親, 經常跟別人講起大姐夫及他們一家人的好。 說大姐苦命, 是因為大姐一生命運坎坷, 先是癱瘓了幾年, 飽受病痛折磨, 后又經歷了丈夫因病早逝的悲痛。大姐夫 49 歲去世后, 大姐一個人, 用柔弱的身軀, 堅強地撐起了一個家。 她含辛茹苦, 帶著膝下二男三女 5 個孩子, 相依為命, 種地養豬, 維持生計, 艱難度日, 并先后為一男三女成了家, 這對于一個山村婦女來說, 是多么不容易啊! 大姐對兒女們的養育之恩, 比泰山還重!
近些年, 在黨和政府以及村組干部各級領導的關心關懷下, 大姐家作為建檔立卡貧困戶, 還安排大姐在村中打掃環境衛生, 每月有五六百元的固定收入, 加上養老金, 尚未成婚的小兒子在外務工也有一些收入, 生活比過去好了許多。 2022 年 8 月、9 月, 我兩次住院做手術, 大姐得知后, 10 月 14 日, 來羊得補吃小妹家女兒的結婚喜酒時, 還特意在本村買了 1 公斤土蜂蜜送給我。 我深知大姐生活不易, 像打架一樣, 大姐才收下我給她的400 元。 現在想來, 如果大姐當時沒有收下我的這點心意, 那將成為我人生中的一大遺憾!
天有不測風云。 由于大姐長期勞累過度, 積勞成疾, 多種疾病疊加, 2023 年 1 月初, 大姐一病不起, 到曲靖市一院住院檢查, 大姐被查出嚴重的白血病。 1 月 14 日, 大外甥給我發來短信說, 無法醫治了, 醫生建議接回家, 留給大姐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真是病來如山倒, 就短短幾天時間, 大姐的生命就沒有挽回的余地了! 當晚, 我給在老家的大哥家打了電話, 告知他們大姐重病的消息, 請他們相互轉告兄弟姊妹幾個, 15 日大姐出院回家后, 相約一起去上普魯看望一下, 畢竟我們姊妹一場。 但因大凌氣候十分惡劣, 道路結冰難以通行, 大姐回家的第四天他們才去看望。 就在這一天——1 月 18 日即農歷臘月二十六, 大姐的心臟永遠地停止了跳動, 走完了她 71 個春秋的人生之旅, 永遠地離開了親人, 離開了她風雨無阻天天早起執帚打掃的環衛崗位! 所有親人和村中父老鄉親都為大姐的突然離世而深感痛惜! 有時候, 人的生命真的很脆弱, 就像一棵草, 說斷就斷了, 又像一盞油燈, 輕輕一吹, 就滅了。
當我得知大姐不幸去世的消息, 心情悲痛萬分。 因住在縣城, 相距百余公里, 當時又下著大凌, 我沒有及時趕到上普魯去看望大姐最后一眼, 直到 10 天后的正月初七火化安葬的頭一天, 我才和妻子、 兒子, 冒著冰天雪地, 一起下去, 最后看到的只是一個裝著大姐遺體的紙棺材了! 淚已流盡, 話未說完, 感嘆人生苦短, 說走就走了!
大姐匆匆地離開了我們, 就像母親、 父親二老和二哥當年走的那樣, 匆忙得沒有留下一句話, 最后留給親人的只有無盡的悲傷和思念!
喜歡文字的我, 利用春節假日, 含淚寫下曾與大姐相處的幾個生活片段, 以告慰九泉之下的大姐, 愿大姐的在天之靈一切安好!
(寫于 2024 年 2 月 14 日至 17 日, 同年在 《珠江源》 雜志第 1期刊載。 2024 年 12 月 24 日又改。 2025 年 2 月 20 日刊于 “掌上
曲靖”, 27 日被河南 《頂端新聞》 轉載。 從整本書考慮, 出版時
刪除了與第一篇相同的一段內容)
【作者簡介】

錢德華,主要筆名:曉勤、田白花,男,漢族,60后,中共黨員,中央黨校本科學歷,1984年9月參加工作,云南富源老廠者米羊得補村人。曾先后任代課教師,生產隊會計,者米大隊計劃生育宣傳員,富源縣廣播站、《曲靖報》(后改為《曲靖日報》)、云南人民廣播電臺和《云南日報》通訊員,富源縣老廠區(鄉)計劃生育助理員,曲靖行署計生委宣傳干部、與《曲靖報》合辦計生專版編輯,富源縣計生委專職秘書,富源縣第四次人普辦秘書組副組長,中共富源縣委宣傳部新聞宣傳科科長,《曲靖日報》富源記者站記者、站長,富源縣第六屆政協委員,富源縣廣播電視服務中心黨支部書記、副主任,富源電視臺《富源新聞》總監,富源縣廣播電視局黨支部副書記、局長,富源縣文化體育廣播電視旅游局黨委書記,《富源人大》《富源潮》副主編,富源縣文聯主席(2016年享受副處職級待遇),富源《勝境文藝》主編,曲靖市文聯第四、第五屆委員、常委,中共富源縣委宣傳部主任科員、四級、三級調研員等職務職級。現為云南省作家協會、評論家協會、攝影家協會和中國職工攝影家協會會員,中國攝影旅游網簽約攝影師,“AIP亞洲國際攝影藝術金牌攝影師”等。2013年至2025年,先后公開出版了《錢德華新聞作品集》(上、下冊)、《宣傳與黨建工作探索》,編印了《光影里的富源紅色之旅》畫冊,在曲靖、富源兩地舉辦過《一個攝影人眼中的巨變——富源縣城北片新區建設錢德華紀實攝影展》,并編印成書,公開出版了詩集《驛路吟唱》《我的胎衣之地》、散文《那些難忘的往事》。在多件新聞、理論、文學、攝影作品獲獎中,詩集《驛路吟唱》獲曲靖市文藝精品創作扶持獎;攝影作品3件獲國際獎銅獎和優秀獎,2件獲國家級金獎和銅獎,13件在省級和全國性攝影賽事中分獲二等獎、優秀獎、百佳獎。1982年至2024年,在先后90多次受到國家和省、市、縣表彰獎勵中,連續6年、10年和10年分別受到《云南日報》社、云南人民廣播電臺和《曲靖日報》社表彰獎勵。1993年實行公務員考核后,11年被考核為優秀,榮立三等功1次。
編輯:詹宇涵
審核:盧志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