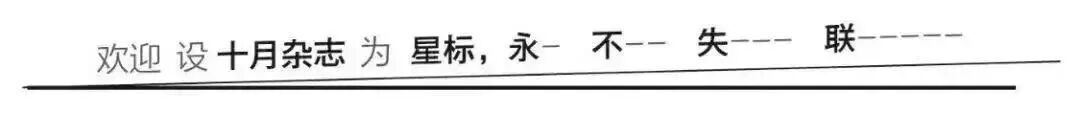
全球首發

阿隆索·奎托
《阿隆索·奎托故事四則》
《十月》2025年第5期

生命的藝術家
這事發生在不久前,我至今仍不知該如何講起。那天我從超市回來,買了些健康食品:一瓶酸奶、橙汁、新鮮奶酪,還有一包蘇打餅干。購物袋沉甸甸的,我正徑直往家走。就在離家不遠的那個公園里,我遇見了一個女人。
她身形纖細,舉止優雅,帶著幾分脆弱,仿佛歷經滄桑。
空蕩蕩的公園里只有我們兩個人。
她走上前和我搭話。
“我經常在這附近見到你,我想,你應該就住在這一帶吧?”
“是的。”我答道。
“我干脆直截了當地告訴你吧,”她盯著我說,“你是唯一能幫助我的人。”
通常遇到這種情況,我會拔腿就跑。但這個女人很美,身上有種特別的氣質。于是我停了下來。
“我要除掉我丈夫。”她補充道。
“好吧。”
超市的購物袋勒得我手生疼。我請她讓我先走,公園里正吹過一陣涼風。
她跟在我身后,繼續說:“只有你能辦到。沒人知道我們相識,甚至沒人知道你的存在。你必須幫我,條件隨你開,任何要求都行。”
“拜托了。”我說。
“你看起來體格健壯,而且飲食健康。我求求你了。”
我深吸一口氣。本該離開的,卻不知為何轉身面對她:“聽著,我不認識你,你顯然瘋得不輕了。我要回家了,抱歉。”
女人僵在原地。我回頭看時,發現她顫抖地站在風里,突然沖我喊出幾聲惡毒的話。我本已走到拐角,但此刻只能繼續向前,筆直地向前。
回到家,我盤算著喝杯啤酒、看會兒球賽、抽支煙,然后睡覺。
突然,電話響了,是我的女朋友。
“親愛的,待會兒我來接你。”
“啊?是嗎?為什么?”
“什么?別告訴我你忘了。今天是我姨媽特蕾莎的命名日,家宴等著我們呢。”
“你說得對,好的。”
我取出啤酒和香煙,又切了片面包。
四點整,女朋友來找我。
“我們去你姨媽家吧?”
“不去了,”她突然說,“我改變主意了。”
“為什么?”
“因為我覺得我們該分手了,”她對我低語,“說實話,和你在一起太乏味了。”
“分手?你要跟我分手?可你剛才還給我打電話說要去你姨媽家的?”
“對,但我之后又想了一下,決定還是分手吧。”
“好吧,但這也太突然了。真令人傷心。”
“別演苦情戲了。”
“行……那就分手吧。不過總得告訴我為什么吧。”
她開始掰著手指數落,一根手指接著一根手指:“你說話無趣,又不愛出門,根本是個可有可無的人。”
這些話刺耳卻真實,我不得不接受。
“行,好吧,那隨你便,親愛的。”
“而且就算我帶你去我姨媽的命名日,你肯定又像往常那樣縮在角落,像個啞巴一樣不和任何人說話。”
“嗯,如果你這么覺得的話。”
“你連句像樣的反駁的話都沒有。我走了。”
我看著她轉身離去,修長的腿劃出優美的弧線,絲綢般憂郁的長發在風中飄散。
我突然淚如雨下。
難道我只能獨自喝著啤酒、抽著煙、看著足球比賽消磨時間?不,還有另一個選擇。
我撥通了妹妹多明蒂拉的電話。她永遠是我在這種時刻的情緒港灣。
不一會兒,我已經在她家了。
“我們喝一杯吧,”她說,“這種時候啤酒最管用。”
“要我從冰箱拿嗎?”
“不,我們去街上。找點兒樂子,走吧。”
妹妹身材高挑,皮膚黝黑,總是笑盈盈的。她是絕佳的陪伴,我非常愛她。
我們出發了。我感覺自己把車開得飛快,行駛在安加莫斯大道上。
一路向前,去尋找快樂。一直向前。
“開慢點兒。”她請求道。
“為什么?”
“因為我們要撞車了。”
就在那一刻,我鬼使神差地轉頭看向她——這至少是個致命的錯誤。
前面的車突然剎車。為了避免追尾,我猛打方向盤。
車子沖出車道,撞上了一根路燈桿。那根粗大的金屬桿已經彎曲,就倒在我們旁邊。
多明蒂拉頭部血流不止,而我卻毫發無傷。我必須尋求幫助,必須救妹妹的命。但在慌亂中,我忘了帶手機。
我沖到人行道上。一些車輛不停地按著喇叭——我們的車禍阻礙了交通。
“該死,”我心想,“該死,該死,該死。”
一個岔路口。
那個陽光明媚的一天,除了刺耳的喇叭聲和車里血流不止的妹妹,整個街區顯得異常寧靜。我想我應該去敲最近那戶人家的門,然后借個電話。必須叫救護車,妹妹的情況看起來很糟。
我走近一棵橡樹旁的房子:木制的大門,大理石臺階,一盞路燈,還有裝著綠色鐵柵欄的窗戶。
我敲了門。
有人透過貓眼看了我。
“求求你,我們出了車禍。我妹妹快不行了。”
突然,門開了。
“真是驚喜。”一張熟悉的面孔對我說。
片刻之后我才反應過來發生了什么。給我開門的竟然是我的老同桌米格爾。我竟然在敲他家的門。
“天啊,多少年沒見了,真是難以置信。”
我走進屋內。
“太巧了,”我說,“請借我電話用用吧。”
“當然可以,不過先和我們喝一杯,”他高聲說道,“正好我們這一屆的好幾個老同學都在。他們肯定不敢相信。”
“可我不能。我妹妹她……”
米格爾拍著我的肩膀,臉上掛著笑容。
突然間,我發現自己已經站在客廳里,被一群又摟又抱的老同學包圍著,他們不停地對我說:“老天,你一點兒都沒變。”
我走到窗邊張望。一輛救護車已經停在外面,醫護人員正把我妹妹抬上擔架。
有人往我手里塞了杯金湯力。
“我得走了,不能待在這兒。”我說,“我得走了,真的很抱歉。”
“至少先干一杯吧。”他們勸道。
不一會兒我終于脫身。我的車還停在那里。我試著發動引擎,成功倒出了事故現場。
我開著這輛保險杠全毀的車,漫無目的地在米拉弗洛雷斯街道上穿行。我得去某家診所找多明蒂拉。
突然,一棵樹倒在我面前。我無路可走。
下車后,我想起了母親。她操勞一生就為讓我過得幸福。就像博爾赫斯詩里寫的那樣,我覺得自己辜負了她。
我在橡樹下哭了起來,想念著我的母親。
我得挽回女友,找到妹妹,還得躲開那個要我幫她殺掉丈夫的女鄰居。
我的人生充滿挑戰,而前路依然漫長。

黎明的藝術家
晨光很美。
枝頭綻滿新蕊,墻垣染上霞色,石墻輪廓漸漸清晰。我看到幾只鳥兒在撲棱棱地飛,溫柔又堅定。它們歌唱,它們飛翔,它們晶亮的眼珠被光芒照亮。
它們仿佛在歡慶某種天賜的喜悅。我想,那是對未來的迎賓曲吧。
是的,這是一個美好的清晨,卻非比尋常。因為今天將是轉折之日。今天我要離開丈夫,與人私奔。
羅德里戈九點會在公園等我。我們約定此前絕不聯系。
啊,羅德里戈,羅德里戈。
私奔。那是個烈日當空的正午,我們在棕櫚樹下的長椅上相擁而泣,立下誓言。
我們特意選了今天,一個出人意料的日子——星期三。沒有人會在星期三和情人私奔,出其不意正是我們的籌碼,看似平庸的一周的中點。
我忐忑、雀躍又幸福,最后一刻難免惶惑。右膝舊傷隱隱作痛,徹夜未眠讓我眼眶發青。
然而,此刻清晨七點半,我正從凌亂的被褥間起身,枕頭散落一地,窗外飄來潮濕的氣息。
我的近處,淋浴的水聲正吧嗒吧嗒濺濕著空氣。
那是我的丈夫。
塞薩爾總是這樣洗澡。他一直這樣活著。我們一直這樣相處——他嘩啦啦濺著水花,而我則聽著他濺水花的聲音。
我離開房間,走下樓,來到廚房。我低頭看著自己的腳——它們永遠在向前走,永遠相信著什么。這雙腳是承載希望的器物。
我往咖啡壺里灌水。這是我最后一次為丈夫煮咖啡了,得煮出最香醇的味道。我找著糖,卻沒有找到他喜歡的紅糖,只找到了白糖。算了,就剩這個了。
“親愛的,”我在樓梯口喊他,“咖啡現在端給你嗎?”
沒有回應。
回到廚房,我把冒著熱氣的咖啡準備好,等著他。他會告訴我要不要加白糖,或者就那樣喝。終究該給他生活里留點甜頭,他需要這個。畢竟我要離開他了,這就是我的想法……
我們沒有孩子,過著尋常夫妻慣有的清寂生活,這只是一種說法罷了。唯一的不尋常,是與羅德里戈相會時他給我的歡愉,我那甜蜜的情人。
但丈夫塞薩爾永遠不會知道。我會等他下樓,像往常那樣,像每天早晨那樣,像每一個該死的早晨那樣——喝完咖啡,告訴我他要遲到了,然后離開家。
料理臺上還擺著三個表皮柔潤的桃子,帶著憂傷的光澤——他總在路上拿這個當早餐。我已打包妥當,等著他帶走。
我看了看表,八點整。再過十三個小時我就能投入羅德里戈的懷抱了:他溫暖的臂膀,饑渴的嘴唇,燃燒的雙眼。
浴室水聲停了。塞薩爾正用力擦拭身體。
快來了。我丈夫穿衣向來迅捷。每天這時候,在城市的某個角落,總有一位女秘書正為他擺放麥克風和水杯,等著他的到來。而助理們正在翻開文件夾,準備著他要向公司高管展示的PPT。在他身邊,咖啡永遠來不及變涼。
塞薩爾系著領帶下了樓,他西裝筆挺,頭發梳得一絲不茍。是的,他像往常那樣對我微笑、道謝、說套話:“我要遲到了,晚點給你電話。”匆匆一吻,又補充道:“事實上,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有時間給你電話。你別等我,我今晚有個很棘手的會議。九點回來,正好趕在宵禁前。”
是啊,又是一個棘手的會議。他總是這套說辭。
他九點回來,正好趕在宵禁前。但今晚這棟房子將不再有我的身影。我決定就這樣消失——不告別、不留字條、不讓他知曉我的去向。不帶任何累贅,只拎個小包,最后望一眼,嘆口氣,然后關門離去。
羅德里戈,我的羅德里戈。九點整,公園里那棵唯一的棕櫚樹下——我們幽會的老地方。在那里我們相會、傾訴、歡笑、纏綿。四周的夜色中,我們的戀情像一道銀色的犁痕。

塞薩爾從未懷疑過我夜半外出。他吞服安眠藥像是吃糖果,然后一覺睡到天亮。
而我總在半夜起身,穿過疫情隔離期間冰冷空曠的街道,快步奔向公園路燈下的約會。偶爾有警車駛過,但沒人發現我們。我們以愛情違抗隔離,卻無人察覺。或許沒人能想象,竟有情侶在凌晨的愛撫與喘息中相會。而我們這樣的日子持續了很久。
直到上周我們下定決心。我們要離開利馬,雖不知去向何方,就乘羅德里戈那輛標致車吧。對于一個四十歲、婚姻乏味的女人,愛上公園里認識的三十歲的男人,私奔是最合理的結局。
一切從一開始就無比自然。
我盤算著今天的行動:瑜伽、健身、給閨蜜打電話、收拾衣物——尤其是那件母親送的白襯衫。然后整理證件、能帶的現金(這些天我每天都從銀行取一點),再把盧倫圣母像揣進手心。
我會在八點半準時出門。最關鍵的是避開與塞薩爾的照面,躲過他計劃的來電。他可能不知道我在哪兒,他會想著是否需要聯系我的姐妹或是朋友。
但塞薩爾絕對不會出來找我,他沒那個膽量——這能為我爭取時間。
因為我要做女人該做的事:我要和那個欣賞我、珍惜我的男人走。那個愛我的男人,我也深愛著他——他就是羅德里戈。
收拾好行李后,我去了藥店,詢問治療膝蓋疼痛的藥膏。可別讓這疼痛在我今晚與羅德里戈床上纏綿時還糾纏不休。我還買了消炎藥,以防萬一,以及一把新牙刷。
剛進家門我就看了看掛鐘,九點整,還有十二個小時。
我端著咖啡坐在窗前。寧靜的風輕撫著中央分隔帶上的樹枝,街道上幾乎不見車輛的蹤影。一道凝固的白光鋪在柏油路面上,折射出我從未見過的奇異光澤。
這場疫情隔離讓現實世界沉寂下來,為沉默騰出了空間——那是由對人類摧毀世界行徑的控訴與孽影交織而成的沉默。人類肆意掠奪自然,這便是自然和諧之神降下的天罰。你們掘我土地,伐我樹木,毀我臭氧。很好,這就是報應。這場瘟疫,它們本是上帝怒焰的天使,被逐出家園后前來索回應得之物。我們罪有應得,全人類都罪有應得。
人類應得這場瘟疫,但我不應如此,我和羅德里戈都應除外。我們是孤獨的魂靈,生來就注定逃離。
我總記得初遇他的場景。那天中午,我如常出門散步,走過兩個街區來到公園。幾個遛狗人牽著他們的黑白貴賓犬,有時喊著狗的名字:麗塔、阿普、迪諾。有位護士推著輪椅上的老先生,戴棒球帽的老人微笑著。幸好所有人都離車道遠遠的。
于是我坐在一株枝條修長的垂柳前,近旁的鳳凰木正開著猩紅的花,更遠處幾叢白色三角梅輕撫著圍墻。突然,公園空無一人,那些貴賓犬、輪椅老人和護士都消失了,唯有青草恣意蔓延的綠,與如小旗獵獵招展的繁花。
就在這不斷蔓延的、無可挽回的寂靜里,我看見他出現了。
我既驚詫又恍惚覺得他熟悉。他走得極慢:步伐沉穩、頭顱高昂、雙手敏捷,深色外套裹著粗硬的短發。一道鋒利的身影,帶著某種戒備的魔力,每個堅定的動作都昭示著他來自未知之境。周遭萬物——樹木、繁花、天空——仿佛都臣服于他。
他即將與我擦肩而過。那一刻,我甚至認定他會徑直走過,而我只求將目光盡可能久地鐫刻在他身上。他本該是個轉瞬即逝的過客,而我,卻注定忘不掉他。
他越走越近。
卻突然停住。
或許因為我的凝視,或許因為我根本無法移開視線。
總之,他停下了,在我身旁的長椅上坐下。
“您在冒險。”他說,“得小心,這里危機四伏。”停頓片刻后他又補充道:“請允許我護送您。”
我沒有應聲。
對話卻繼續進行。
“我總見您在這兒,這地方很美。”羅德里戈初次與我相遇時這么說。
他深色的皮膚泛著光澤,瞳孔里躍動著光,藍色外套襯著雪白領口,頭顱始終保持著警覺的昂起姿態。他用信徒般的專注凝視我。
是的。自那以后,我們在長椅相會了好幾次。
至今我仍不知羅德里戈棲身何處,他也從未踏足我的住所。那棵棕櫚樹下的公園長椅,才是我們共同的家。直到今晚——我們將奔赴某個遠方。直到這個星期三的夜晚——我們將攜手開始新生。
行李早已收拾妥當。
愛的反面從來不是恨,而是絕望。
(未完)
作者簡介
阿隆索·奎托(Alonso Cueto),秘魯著名作家。畢業于美國德克薩斯州大學,回到秘魯后,成為El Comercio和Debate雜志的定期撰稿人,同時還在利馬天主教大學擔任文學系博士生導師。在他的職業生涯中,曾經獲得過2005年赫拉爾德小說獎等重要獎項。他的作品被翻譯成數十種語言,被認為是秘魯當今最重要的文學作家。

溫馨提示
由于微信公眾號修改了推送規則,所以部分關注本號的朋友無法在第一時間收到“十月雜志”公號推送的消息。
歡迎各位朋友按下面的方法簡單設置,讓本號繼續為您在第一時間及時進行推送:
?關注并進入公眾號
?點擊手機右上角“. . .”。
?點擊“設為星標”。
?這樣您就可以及時收到本公眾號推文。

悅-讀
全球首發 | 科爾姆·托賓:長島
全球首發 | 阿蘭·貝內特:住面包車的女人
全球首發 | 賽爾喬·比奇奧:一生的愛(范童心 譯)
全球首發 | 馬加里托·奎亞爾的詩(孫新堂 譯)
全球首發 | 安德烈斯·伊巴涅斯:一種更高的生活(楊玲 譯)
長按識別二維碼,購買《十月》新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