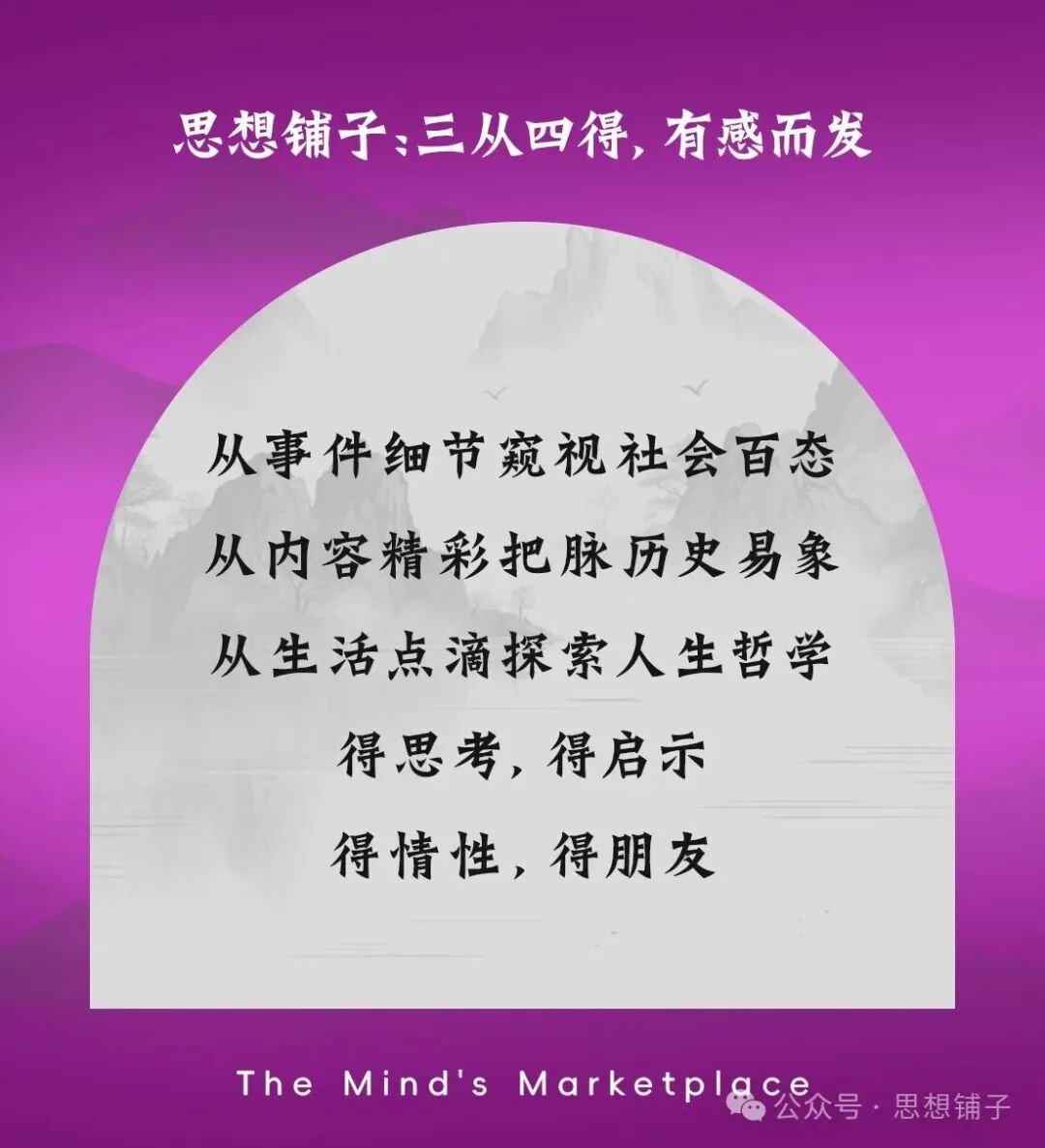編者的話:當下,是“適當的放下”
前兩天收到鋒兄文稿時,我剛好在老家。辦完事情后,我順便回家看看父母。
或許是看了此文的緣故,這次與父母短暫的相聚,觸景生情。
父親年過八旬,皺紋堆積的溝壑,深藏歲月的滄桑;母親濃密的黑發里,白發已開始“怒放”。
我們仨早早吃過晚飯,聊聊家常。父親依然熱衷天下時事,而母親則有做不完的家務瑣事。雙親雖老去,他們對生活的熱愛,他們對子女孫輩的關懷和關注,仍然舐犢情深。
鋒兄在文中說:“父母的叮嚀,愛人的絮語,朋友的陪伴,時間長了,像呼吸一樣自然,也像空氣一樣被忘卻。”
他的提醒,讓我如夢初醒。快意生活的我們,是否適當放下一些執念,常回家看看父母,或者與愛人多說心里話,或者三五知己尋覓更多的心靈溝通。
閱讀別人,往往也內觀了自己。珍惜當下,是讓自己適當放下。
《好了傷疤忘了痛》
周末,整理一下無暇顧及的書柜。手指拂過蒙塵的書脊,好像觸摸到了一縷并不陌生的悵惘。
有些書,買回來后便束之高閣。在我們心中,在“擁有”的那一刻,書便完成了它的使命。書中的黃金屋與顏如玉,從此在書架上沉睡。
這或許是人生的常態:擁有時,不知珍惜;失去時,方覺可貴。
我們總是熱衷于奔向遠方未點燃的火。窗前溫暖的燈,淪為自己視而不見的背景。
這是一種奇怪的盲目。
一
痛,可以擊破這種盲目。
它像一塊燒紅的鐵,不由分說地烙在你的記憶上,嘶嘶作響,還發出燒焦的氣味。那時你發誓:只要痛楚離去,愿意付出任何代價,也會永記此刻的煎熬。
痛是真的走了。灼熱的高溫漸漸變冷,尖銳的棱角被時光磨圓,最后只留下一塊光潤的疤痕,像一枚模糊的郵票,貼在往事的信封上。
我是左撇子,右手有不少傷疤。偶爾撫摸著它,記得痛過,記得事故的始末,卻再也喚不回痛的本體。
我們已經大膽地將當初的誓言忘得一干二凈。
這種遺忘,難道不是慈悲的天賦?要不然,一次生產的痛就足以讓母親拒絕第二次懷孕;一場失戀就足以讓心靈永遠冰封。
是這“好了的傷疤”,這奇妙的“忘痛”,給了我們重新涉足人間的勇氣。
二
對待健康,我們便是如此。當健康屬于我們時,它是一口深井,我們只管汲取清冽的泉水,從沒想過低頭望一眼水源。
直到某天,身體發出“砰”一聲沉悶的、生銹的異響,我們才猛地驚醒。那一直隱身的“健康”,像退休的仆人,站到你面前,用沉默的、責備的眼神,向你提醒它長久以來的服務。
人與人的情誼,也是這般。我們的目光總是投向窗外流動的風景。父母的叮嚀,愛人的絮語,朋友的陪伴,時間長了,像呼吸一樣自然,也像空氣一樣被忘卻。
其實,我們還活在更深刻的痛楚里。這“痛”,名為“失去”。
我們擁有美妙的時光和健壯的身體,還有村口榕樹永不消散的濃蔭和母親高聲的呼喚。因此我們無度地揮霍,像億萬富翁肆意揮霍金幣。我們深信家的港灣,有燈永遠亮著。
直到有一天——那一天總是會到來——疾病如不速之客,讓你在深夜清晰地聽見的自己心跳,你才發現世界竟如此空曠;直到老樹被伐倒,陽光一下子砸在地上,白得晃眼,你才驀然看見,原來心里的一片天地,全靠它的枝葉撐起。
這時,“失去”的痛楚才真正到來。它比一切肉體之痛更鋒利,因為它沒有傷疤,只在心里留下一個空洞。
風從洞穿過,發出嗚嗚的聲響,全是往日的回音。
回憶在此時開始施展巫術。那些漫不經心度過的往日,在“失去”這面黑板上,煥發出神異的光彩。一聲瑣碎的嘮叨,一次無謂的爭執,都變得溫情脈脈。
我們成了詩人,用悔恨與懷念的筆,將自己平凡的經歷改寫得無比動人。
這前后的反差,這“在”與“不在”之間的鴻溝,既仁慈又殘酷。
仁慈,是它讓我們從痛苦記憶中解脫,像愈合傷疤,給我們繼續前行的勇氣;殘酷,是它讓我們在幸福中麻木,非要以“失去”為代價,才能測量到幸福的深度。
古人教我們“居安思危”,是要在鐘擺蕩向安適的頂點時,給它清醒的、向下的力量,以免它蕩得太高,摔得太重。
這道德箴言,讓我們在晴空聽見遠方的雷聲,在擁抱時感知別離的寒意。
三
我們并不是要杜絕“擁有時遺忘,失去時追憶”的人性循環,而是要在這循環里,多添幾分自覺。
我們不用終日戰戰兢兢,憂慮失去,而是要學著做自己生活的“旁觀者”,帶著一絲即將離別的惆悵,來度過眼前的每一刻。
就像在晴朗的秋日,坐在花園里,知道寒冬終將來臨,所以用心感受陽光的溫暖,仔細端詳最后一朵玫瑰的顏色。
現在,我就可以用心感受這一刻——安穩的書桌,柔和的燈光,思想在萬籟俱寂中如小魚輕輕躍出水面。
我學會珍惜,不必等到它們成為追憶。
當“失去”不可避免地降臨時,我們或許能少一些頓足的悔恨,多一些寧靜的感激。感激那曾經擁有過的、被我們真正“看見”過、并深深愛過的一切。
如果我們能真切地感受過光的溫暖,黑夜便不再是純粹的虛無,而是滿載光明的黑暗。
感謝您耐心閱讀完本文。
聲明:文章來源于王鋒作品,圖片由豆包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