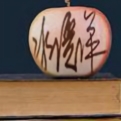第二十四章:國(guó)聯(lián)的命運(yùn)(1)
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四日,巴黎和會(huì)全體會(huì)議。美國(guó)總統(tǒng)伍德羅·威爾遜站在凡爾賽宮鏡廳的講臺(tái)上,手中高舉著《國(guó)際聯(lián)盟盟約》草案,用讓人聽(tīng)起來(lái)好像有點(diǎn)激動(dòng)的聲音鼓動(dòng)著:“先生們,我手中的不僅是一份文件,這是世界的良知!它將終結(jié)一切戰(zhàn)爭(zhēng),建立永久的正義!”水晶吊燈的光芒照在草案的文本上,仿佛真的散發(fā)著正義的光輝。
臺(tái)下,法國(guó)總理喬治·克列孟梭戴著灰色手套的雙手交叉抱于胸前,閉目養(yǎng)神。
英國(guó)首相戴維·勞合·喬治低頭在筆記本上畫(huà)著一艘船的草圖——他剛剛收到電報(bào),皇家海軍在北海又?jǐn)r截了一艘德國(guó)走私軍火的船只。
當(dāng)威爾遜講到“公開(kāi)外交”“民族自決”時(shí),日本全權(quán)代表牧野伸顯微微調(diào)整了眼鏡的位置,鏡片后的目光落在草案第四章第二十二條的位置。那里有個(gè)鉛筆做的微小記號(hào),是他昨晚與英國(guó)代表團(tuán)法律顧問(wèn)“非正式溝通”后留下的。條文草案寫(xiě)著:“前屬土耳其帝國(guó)之各民族……其發(fā)展已達(dá)可暫被承認(rèn)為獨(dú)立國(guó)之程度……”
“暫被”——這個(gè)詞,在法律上,這意味著無(wú)限期的拖延。而關(guān)于太平洋島嶼的段落,草案巧妙地使用了“其居民尚不適宜自治”的表述。他把這頁(yè)草案折了個(gè)角,遞給身后的秘書(shū),勾了幾下手指,示意秘書(shū)靠近,低聲用日語(yǔ)說(shuō):“告訴倫敦的朋友,這個(gè)表述……可以接受。”
兩周后,盟約起草委員會(huì)第四小組的會(huì)議室正在開(kāi)會(huì)。主持人是英國(guó)代表、南非總理?yè)P(yáng)·史末資——一個(gè)曾在布爾戰(zhàn)爭(zhēng)中與英國(guó)人作戰(zhàn),如今卻代表大英帝國(guó)的復(fù)雜人物。
“先生們,”史末資站在講臺(tái)上,面向臺(tái)下的幾位說(shuō),“我們必須把威爾遜總統(tǒng)高尚的原則,轉(zhuǎn)化為可操作的法律條文。我提議,將前敵國(guó)屬地分為三類(lèi)。”
他轉(zhuǎn)身在黑板上寫(xiě)下:
A類(lèi):前屬土耳其地區(qū),“其發(fā)展已達(dá)可暫被承認(rèn)為獨(dú)立國(guó)之程度”(阿拉伯地區(qū))
B類(lèi):中非地區(qū),“委任統(tǒng)治國(guó)須負(fù)行政之責(zé)”
類(lèi):西南非洲及太平洋島嶼,“鑒于其地小人稀、距文明中心遙遠(yuǎn)……可視作其領(lǐng)土之一部分施行治理”
法國(guó)代表安德烈·塔迪厄立刻質(zhì)疑:“‘視作其領(lǐng)土之一部分’?這等于承認(rèn)吞并!與盟約精神相悖。”
史末資微笑著:“不,塔迪厄先生。這只是在特定條件下的‘治理方式’。法律上,主權(quán)仍屬?lài)?guó)聯(lián)。”但所有人都聽(tīng)懂了潛臺(tái)詞:法律上的主權(quán)是虛幻的,實(shí)際的控制才是永恒的。
晚上8點(diǎn)15分:史末資的秘書(shū)將文件裝進(jìn)了外交郵袋。他不知道,郵袋的鎖扣在三天前已被法國(guó)情報(bào)部門(mén)做了手腳,復(fù)制鑰匙只需要兩分鐘。
晚上10點(diǎn)30分:法國(guó)特工取走文件,在圣日耳曼區(qū)一間安全屋快速拍照。拍照時(shí),特工注意到草案邊緣有一行手寫(xiě)鉛筆字:“此條已獲東京方面原則同意,澳、新無(wú)異議。”他特意給這行字一個(gè)特寫(xiě)。
凌晨1點(diǎn):照片沖印兩份。一份送往法國(guó)殖民部,另一份——按照馬庫(kù)斯與法國(guó)情報(bào)線人的秘密協(xié)議——被送往柏林。
次日上午9點(diǎn):馬庫(kù)斯在柏林辦公室看著照片,目光落在那行鉛筆字上。“東京方面原則同意……”他自語(yǔ)道,然后按下呼叫鈴:“給我們?cè)谌諆?nèi)瓦的人發(fā)電報(bào):接觸日本代表團(tuán)中不滿當(dāng)前山東問(wèn)題處理結(jié)果的成員,暗示他們——英國(guó)人在用太平洋島嶼的交易,換取日本在山東問(wèn)題上的沉默。”
他的判斷精準(zhǔn),三天后,日本代表團(tuán)內(nèi)部分裂的消息傳回:一部分人認(rèn)為應(yīng)集中火力爭(zhēng)取山東,另一部分則希望確保太平洋利益。內(nèi)部分歧,從來(lái)都是外部滲透的最佳入口。
又一過(guò)了周后,起草會(huì)議陷入膠著。日本代表堅(jiān)持要在C類(lèi)條款中,明確寫(xiě)入“委任統(tǒng)治國(guó)應(yīng)保障當(dāng)?shù)鼐用駛鹘y(tǒng)生活方式”——看似人道,實(shí)則意在為日本在太平洋島嶼實(shí)施嚴(yán)格管控、限制外來(lái)影響提供法理依據(jù)。
英國(guó)代表、外交官羅伯特·塞西爾勛爵面露難色。此時(shí),他的秘書(shū)遞來(lái)一張紙條,上面只有三個(gè)詞:“山東-沉默-島嶼”。
塞西爾瞬間明白了。休會(huì)時(shí),他在吸煙室“偶遇”牧野伸顯。
“關(guān)于太平洋島嶼居民的保護(hù)條款,”塞西爾點(diǎn)上雪茄,“我們認(rèn)為可以加入,但措辭需要……謹(jǐn)慎,以免被誤解為限制委任統(tǒng)治國(guó)的必要管理權(quán)。”
牧野往眼鏡片上哈了口氣,認(rèn)真地擦拭著,慢條斯理地說(shuō):“當(dāng)然,必要的管理權(quán)必須保障。就像在山東,日本也必須擁有維持秩序的必要權(quán)限。”
兩人對(duì)視,沉默了三秒。雪茄煙霧在空中漂出流暢的線條。
“我相信,”塞西爾緩緩說(shuō),“合理的條款總能找到合理的表述。也許我們可以約定,不在盟約中討論……特定區(qū)域的具體問(wèn)題?”
牧野戴上眼鏡后說(shuō):“這是明智的。有些問(wèn)題,留待……適當(dāng)?shù)碾p邊渠道解決更為妥當(dāng)。”
這場(chǎng)對(duì)話從未出現(xiàn)在任何會(huì)議記錄中。但它決定了日本在盟約中支持英國(guó)的C類(lèi)條款表述,換取英國(guó)在山東問(wèn)題上不作梗的默契。一筆用法律條文進(jìn)行的領(lǐng)土交易,就這樣達(dá)成了。
四月,討論轉(zhuǎn)向國(guó)聯(lián)行政院的決策機(jī)制。法國(guó)代表萊昂·布爾熱瓦——一位白發(fā)蒼蒼的法學(xué)家,看上去像位慈祥的祖父——提出了最冷酷的建議:
“行政院的任何決議,包括常任理事國(guó)在內(nèi)的全體成員必須一致同意。”他敲打著黑板說(shuō),“這是防止國(guó)聯(lián)被濫用的唯一保障。”
美國(guó)代表、前總統(tǒng)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立即表示反對(duì):“這將使國(guó)聯(lián)在任何重大問(wèn)題上癱瘓!如果一個(gè)侵略者的盟友在行政院,它就可以用否決權(quán)保護(hù)侵略者!”
布爾熱瓦微笑:“那么請(qǐng)問(wèn),如果多數(shù)票就能決定,大國(guó)為什么要加入一個(gè)可能被小國(guó)聯(lián)盟挾持的機(jī)構(gòu)?”
布爾熱瓦的強(qiáng)硬立場(chǎng)并非孤軍奮戰(zhàn)。會(huì)議期間,法國(guó)軍情二局的特工在巴黎黑市上,秘密收購(gòu)了奧匈帝國(guó)解體后流出的部分外交密碼本。他們用這些密碼本,向中東歐新獨(dú)立國(guó)家的外交部發(fā)送匿名信,信中“透露”:
“據(jù)悉,英國(guó)意圖在國(guó)聯(lián)推行多數(shù)決,以便與其自治領(lǐng)(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形成固定投票集團(tuán),操控小國(guó)。法國(guó)全力捍衛(wèi)‘全體一致’原則,正是為保護(hù)小國(guó)不被大國(guó)聯(lián)盟壓迫。”
這招極其陰險(xiǎn)。一方面,法國(guó)在公開(kāi)場(chǎng)合以“保護(hù)大國(guó)權(quán)益”為由支持否決權(quán);另一方面,暗中以“保護(hù)小國(guó)”為名游說(shuō),將英國(guó)塑造成霸權(quán)野心家。數(shù)個(gè)小國(guó)代表的態(tài)度開(kāi)始搖擺。
馬庫(kù)斯很快通過(guò)維也納的渠道獲知了這些匿名信。他沒(méi)有阻止,反而添了把火:他讓手下模仿英國(guó)筆跡,向同樣幾個(gè)小國(guó)發(fā)送“澄清信”,語(yǔ)氣傲慢地表示“國(guó)聯(lián)決策效率至關(guān)重要,小國(guó)應(yīng)信任大國(guó)的領(lǐng)導(dǎo)”。
結(jié)果可想而知:小國(guó)代表更加確信大國(guó)(尤其是英國(guó))心懷不軌,紛紛倒向法國(guó)支持的“全體一致”原則。否決權(quán)條款的阻力大減。
真正讓否決權(quán)條款一錘定音的,是克列孟梭與勞合·喬治的一次私人晚餐。
“戴維,”克列孟梭一邊切著牛排說(shuō),“德國(guó)現(xiàn)在趴下了。但十年后呢?二十年后呢?如果德國(guó)有一天重回行政院,而國(guó)聯(lián)可以多數(shù)票通過(guò)對(duì)法國(guó)不利的決議……你會(huì)怎么選?”
勞合·喬治沉默。他知道克列孟梭在說(shuō)什么:萊茵蘭非軍事區(qū)的未來(lái)、薩爾區(qū)的歸屬、德國(guó)的重整軍備……任何風(fēng)吹草動(dòng)都可能被提到國(guó)聯(lián)。而英國(guó),可能需要在“支持法國(guó)”和“安撫德國(guó)”之間做選擇。
“全體一致原則,”克列孟梭放下刀叉,“不是針對(duì)現(xiàn)在的德國(guó)——它沒(méi)資格進(jìn)來(lái)。是針對(duì)未來(lái)的德國(guó),以及……任何可能在未來(lái)與法國(guó)立場(chǎng)不一致的朋友。”他意味深長(zhǎng)地看著勞合·喬治。
勞合·喬治最終點(diǎn)了點(diǎn)頭。他想到的是大英帝國(guó)的全球利益:香港、新加坡、蘇伊士運(yùn)河……如果國(guó)聯(lián)可以用多數(shù)票干涉“內(nèi)政”,那殖民地的任何動(dòng)蕩都可能被國(guó)際化。
當(dāng)晚的餐桌談話沒(méi)有記錄。但第二天,英國(guó)代表團(tuán)對(duì)否決權(quán)條款的反對(duì)聲明顯減弱。 法國(guó)用未來(lái)的德國(guó)威脅,觸動(dòng)了英國(guó)對(duì)自身帝國(guó)安全的深層恐懼。
五月,會(huì)議接近尾聲。一份來(lái)自東京的緊急電報(bào)被送到牧野伸顯手中。電文核心是:“必須確保盟約不損害帝國(guó)在支那之特殊權(quán)益。區(qū)域諒解條款為生命線。”
幾天后,牧野在討論“盟約與其他條約關(guān)系”時(shí),突然發(fā)言:“我們必須承認(rèn),世界上存在一些歷史形成的區(qū)域諒解,它們維護(hù)了特定地區(qū)的和平。比如……門(mén)羅主義。”
美國(guó)代表一愣。門(mén)羅主義是美國(guó)獨(dú)霸美洲的宣言,從未得到國(guó)際條約正式承認(rèn)。
牧野繼續(xù)說(shuō):“如果這樣的區(qū)域諒解因盟約而受到質(zhì)疑,將引發(fā)嚴(yán)重的不穩(wěn)定。我提議增加條款:‘本盟約之任何規(guī)定,不得視為影響國(guó)際協(xié)定如仲裁條約或區(qū)域諒解……之效力。’”
會(huì)議室安靜了。所有人都聽(tīng)懂了:日本要以“門(mén)羅主義”為模板,為自己在亞洲的“特殊權(quán)益”尋求同樣的豁免地位。
爭(zhēng)論持續(xù)數(shù)日。英國(guó)起初猶豫,擔(dān)心這會(huì)削弱國(guó)聯(lián)權(quán)威。直到六月三日那個(gè)戲劇性的下午。
在一次小范圍磋商中,日本副代表珍田舍己博士看似無(wú)意地打開(kāi)公文包,取出一份文件。文件滑落在地,他匆忙撿起,但坐在對(duì)面的美國(guó)法律顧問(wèn)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已經(jīng)看到了——那是一份文件的扉頁(yè),抬頭是英文:
“1917年英日秘密備忘錄”
更刺眼的是下面一行手寫(xiě)標(biāo)注:“關(guān)于山東權(quán)益”。
珍田博士迅速收起文件,連聲道歉。但傷害已經(jīng)造成,杜勒斯臉色鐵青。他知道那份密約的存在——戰(zhàn)時(shí)英國(guó)為換取日本海軍支持在地中海護(hù)航,確實(shí)在山東問(wèn)題上做出過(guò)模糊承諾。但看到白紙黑字,沖擊完全不同。
會(huì)后,英國(guó)代表團(tuán)召開(kāi)緊急會(huì)議。塞西爾勛爵接到來(lái)自倫敦最高層的指示:“避免在任何場(chǎng)合公開(kāi)討論1917年諒解。區(qū)域諒解條款……可予考慮。”
六月六日,第二十一條的最終表述敲定:
“本盟約之任何規(guī)定,不得視為影響國(guó)際協(xié)定如仲裁條約或區(qū)域諒解……之效力。”
“區(qū)域諒解”這個(gè)詞被刻意保留了模糊性。它可以是門(mén)羅主義,也可以是任何大國(guó)宣稱(chēng)的“特殊利益范圍”。
簽字前夜,牧野伸顯在日記中寫(xiě)道:
“今日最大收獲:第二十一條通過(guò)。西方人為門(mén)羅主義開(kāi)的后門(mén),將成為帝國(guó)在東亞門(mén)戶(hù)的合法鎖鑰。法律之妙,在于一詞多義;外交之勝,在于心照不宣。威爾遜總統(tǒng)的‘新外交’,終被舊世界的秩序?qū)懢汀!?br>
而與此同時(shí),在柏林,馬庫(kù)斯正對(duì)鐵十字會(huì)亞洲事務(wù)負(fù)責(zé)人說(shuō):
“記住今天這個(gè)條款。它不是結(jié)束,是開(kāi)始。當(dāng)日本用這個(gè)條款在亞洲擴(kuò)張時(shí),我們就能用同樣的邏輯,在歐洲爭(zhēng)取‘生存空間’。法律是他們寫(xiě)的,但游戲……將由我們重新定義。”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國(guó)際聯(lián)盟盟約》作為《凡爾賽條約》第一部分,在鏡廳正式簽署。威爾遜總統(tǒng)臉上洋溢著理想主義者的光輝。他不知道,也不會(huì)知道:
在他高舉的盟約第二十二條里,殖民主義借尸還魂,被分類(lèi)學(xué)和法律術(shù)語(yǔ)精心包裝。
在第五條里,大國(guó)為自己安裝了永遠(yuǎn)的安全閥,確保這個(gè)新生的國(guó)際機(jī)構(gòu)從基因里就無(wú)法反抗它的創(chuàng)造者。
在第二十一條里,一道為美國(guó)歷史政策開(kāi)啟的后門(mén),將成為所有帝國(guó)未來(lái)擴(kuò)張的合法通道。
鏡廳的十七面鏡子,照出簽署者的身影,卻照不見(jiàn)那些在煙霧繚繞的密室里、在密碼傳輸?shù)碾姴ㄖ小⒃诨涞孛娴拿孛芪募希缫淹瓿傻恼鎸?shí)交易。
國(guó)際聯(lián)盟誕生了。帶著榮耀的宣言,也帶著胎里帶來(lái)的毒藥。而最先品嘗這毒藥滋味的,將是那些相信了宣言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