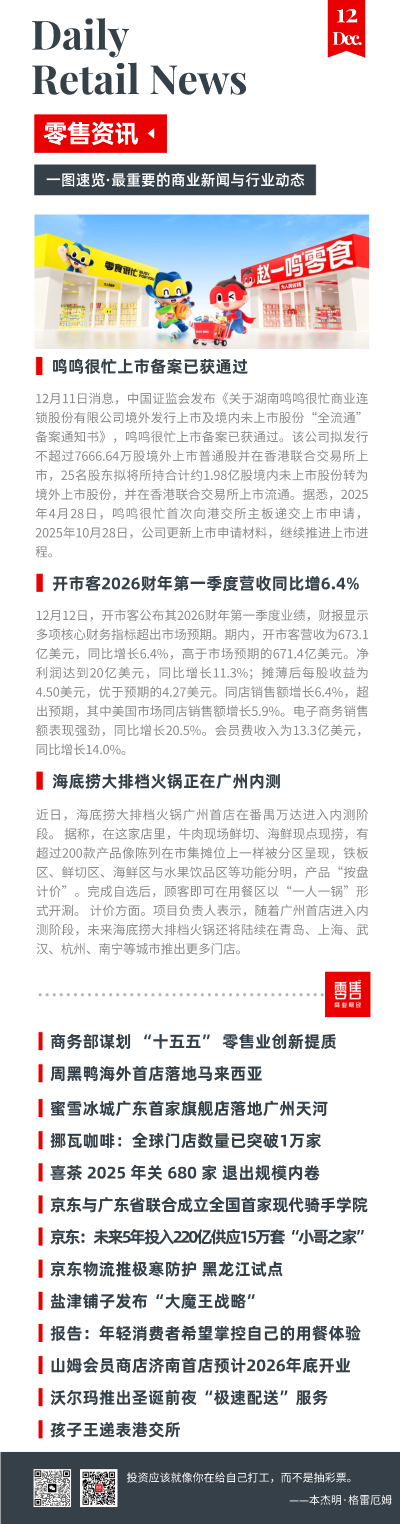燈火把貨架澆鑄成琉璃,
價簽如薄荷糖紙般閃爍。
八毛錢的棒棒糖列隊敬禮,
它們確信自己正甜透,
某個孩童攥緊紙幣的黃昏。
但我分明看見,
紅底招牌在暮色里擴張暗影。
它吞下隔壁商鋪的氣喘,
消化成進貨單上,
一行帶刺的利潤。
穿短袖的店員擦拭薯片袋,
冷氣在他額角制造出,
小型人工降雨。
貨箱持續吐出膨化食品,
像吐出被壓平的云朵,
它們膨脹的欲望,
恰好填滿貨架間,
精確計算的虛空。
收銀機吐出的單據越來越長,
長過返鄉鐵路上,
那些數著回本周期的,
不眠的夜晚。
加盟合同在抽屜里,
與賬本相互質疑,
直到卷閘門,
拉下鐵青的判決。
資本在財報上游泳,
而貨架深處,
某包延期三個月的餅干,
正學習用油脂香精,
模擬春天。
當掃碼槍“滴”聲響起,
整個店鋪的燈光忽然暗了一瞬,
像龐大消化系統里,
一次尋常的腸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