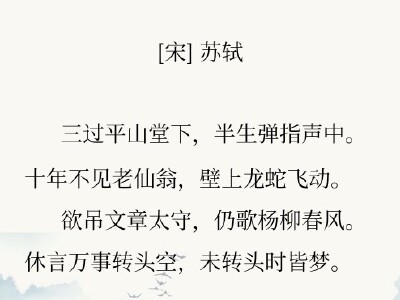西江月·勝之
蘇軾
別夢已隨流水,淚巾猶裛香泉。
相如依舊是臞仙,人在瑤臺閬苑。
花霧縈風縹緲,歌珠滴水清圓。
蛾眉新作十分妍,走馬歸來便面。

這是蘇軾寫給勝之的第二首《西江月》,也是寫給勝之的第四首詞,也是最后一首。
元豐六年(1083)八月,徐君猷任滿去湖南任職,蘇軾與暫時還留在黃州的徐君猷的家人一起為之餞行,并作《好事近》一詞。
紅粉莫悲啼,俯仰半年離別。
看取雪堂坡下,老農夫凄切。
明年春水漾桃花,柳岸隘舟楫。
從此滿城歌吹,看黃州闐咽。
歌詞大意是,你們就別再悲悲啼啼了,真正應該悲啼的是我。半年的時間,一晃就過去了。但我就不一樣了,能不能再見面只有天知道。知心的朋友不能再相見,這才是世間最令人捶胸頓足、傷感痛苦的事,若不信,半年后,當黃州百姓“滿城歌吹”地送走你們,你們再看雪堂坡底下那個孤獨的老農夫,會凄涼悲切到了什么程度。
豈料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徐君猷竟客死任途,這一別,也成永訣。
元豐七年(1084)年正月,蘇軾量移汝州,四月一日離黃動身去新的貶所。當他六、七月間走到姑熟(今安徽省當涂縣)時,意外地又遇到勝之。不過此時的勝之,已另有所歸。南宋王明清所撰《揮麈后錄》中有段記載云:
君猷后房甚盛,東坡嘗聞堂上絲竹,詞中謂“表德原來字勝之”者,所最寵也。東坡北歸,過南都,其人已歸張樂全之子厚之恕矣。厚之開燕,東坡復見之,不覺掩面號慟,妾乃顧其徒而大笑。東坡每以語人,為蓄婢之戒。
見到勝之,蘇軾想到死去的徐君猷,是自然的事,“掩面號慟”也在情理之中;同樣,見到蘇軾,勝之肯定也會想到徐君猷,但她竟“顧其徒而大笑”,難道戲子真的無情嗎?
蘇軾便寫了此首《西江月》。
“別夢”,即離別后在夢中又夢到離別時的情景。俗話說: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別夢已隨流水”,是說勝之已不再思念徐君猷。“淚巾猶裛香泉”,這句是詞人的回憶之語。“香泉”,美喻勝之的眼淚。黃州送別徐君猷時,勝之淚水如泉涌,濕透了手帕。“猶裛”,即手帕還涅涅的,沒有干。這兩句寫得比較婉轉,有怨的味道,但沒有怒。即便怨,也是替徐君猷而怨,因對徐君猷愛之深,愛屋及烏的怨。在古代,女子一旦淪為歌伎,便注定了一輩子寄人籬下、看人臉色的生活。蘇軾是個通情達理之人,最懂人情世故。他在徐家宴會上見到的勝之才十四歲。一個十四歲的如花似玉的小姑娘,還不諳人事便做了小妾,服侍著一個頭發花白的糟老頭子。這本來就讓人心里噎噎的,況且現在人已經走了半年多了,你還奢望她仍是淚眼汪汪的,不現實。如果因此而責備她,便是不近人情。上片后二句中,“相如”是詞人代稱自己,“人”指徐君猷。司馬相如認為“儒居山澤間”的列仙,通常被描述為形體容貌清瘦,這不符合帝王對仙人形象的期待。故詞人說,我還是那個我,沒什么變化。雖說量移汝州,皇上有點原諒自己了,但還是“山澤間”一個“臞仙”,一個行動不自由,也不管事的團練副使;徐君猷雖然已離開人世,到了西方極樂世界,但我未嘗不思念他。變的,變得如此之快;不變的,又變得如此之慢。世事的變化真讓人難以捉摸,這不能不令詞人心生感慨。
詞的上片因勝之而發,全用虛筆,寫世事變化無常,難以預料。下片詞人則將鏡頭聚焦宴會,具體描繪當涂遇到的勝之。頭兩句用比喻,描繪其歌舞。前句謂勝之旋轉起來,舞姿輕盈柔美,猶如在風中飄揚,人就像是霧中開放的花朵一樣。后句謂她的歌喉如貫珠,如滴水,清亮而圓潤。尾二句則用張敞畫眉事,喻勝之歸張氏后又為張恕所寵愛,故云“蛾眉新作十分妍”。又用張敞走馬章臺事,寫勝之為避免與蘇軾見面后的尷尬,就用便面遮擋住了自己的臉。雖是一個小小的舉動,卻寫出了勝之復雜的心理。由此可見,勝之確是個“海里猴兒”,并非如王明清記載的那樣無情無義。
除了自己的侍妾王朝云,在朋友侍妾中,勝之是蘇軾為之贈詞最多的一個。個中原因自然是因為徐君猷。徐君猷是蘇軾人生路途上第一次受到致命打擊,貧困交加,親朋斷絕往來之時,第一個伸出援手的人。愛屋及烏,夸夸主人的美妾,也是人之常情。況且這樣一個美人,誰見了都會喜歡,如果不喜歡,會讓人懷疑其神經是不是有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