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閱讀的故事:
尋找丁香
刁仁慶
1979年的春天,我在部隊服役。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在《中國青年》雜志上讀到一篇小說《感情》。可以這樣說,這篇小說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血液里。它對我的文學創作觀念起到了至關重 要的作用。小說里邊有一個細節,使我在很多部小說創作中進行了多次借鑒翻新運用——既用在《流金歲月》中,也用在《于無聲處》紅色系列作品中。
這個細節是:“晶瑩透明的酒杯瞬間碰在了一起,酒漿濺灑出來,酒滴交融,又落在杯中,帶著馨香流進心田,在心底燃燒起感情的火焰。……”
一般讀者應該不會對這種淡淡的細節留下深刻印象,可我卻偏偏記住了這個細節。為什么呢?當時我也說不清楚。后來想想,《感情》這篇小說是“傷痕文學”,寫青年姑娘丁香對那段特殊時期的反思、悔恨和批判。看似是寫人生命運的悲傷,實則是寫時代的悲劇。隨著時間的推移,作品里邊的很多細節我都記不起來了,唯獨記住了這個細節,當然也記住了作品主人公丁香的名字。
四十多年來,我一直想再重讀這篇小說。但是,我只知道它是在1979年《中國青年》雜志上刊登的,卻不知道是哪一期。后來我把這篇小說的名字也忘了,我認為小說的名字就叫《丁香》。隨著互聯網的發展,我多次在網上搜索“丁香”二字,但怎么也搜索不到。作者是誰也記不起來了。再后來我到多個網站搜索1979年《中國青年》合訂本,但是售書網上搜遍也找不到。我只好在網上買了幾期零散的1979年《中國青年》,但是這些雜志里邊也查不到這篇小說。特別是我退休以后,愈發想再閱讀這篇小說。然而,往哪里找這篇小說呢?我長時間地反復推敲,想,它是不是刊登在1978年的《中國青年》雜志上呢?于是就在網上購買1978年的《中國青年》雜志。原來,1978年的《中國青年》雜志總共只出版了4期。第1期是復刊號,復刊號是1978年9月發行的。后來人們才知道,這一年的《中國青年》復刊號還引起了巨大的風波,這是題外話。大家可以在網上搜索“《中國青年》雜志復刊號風波”便知道了。隨后出了三期,我都購買到了,查遍這4期雜志也沒有發現這篇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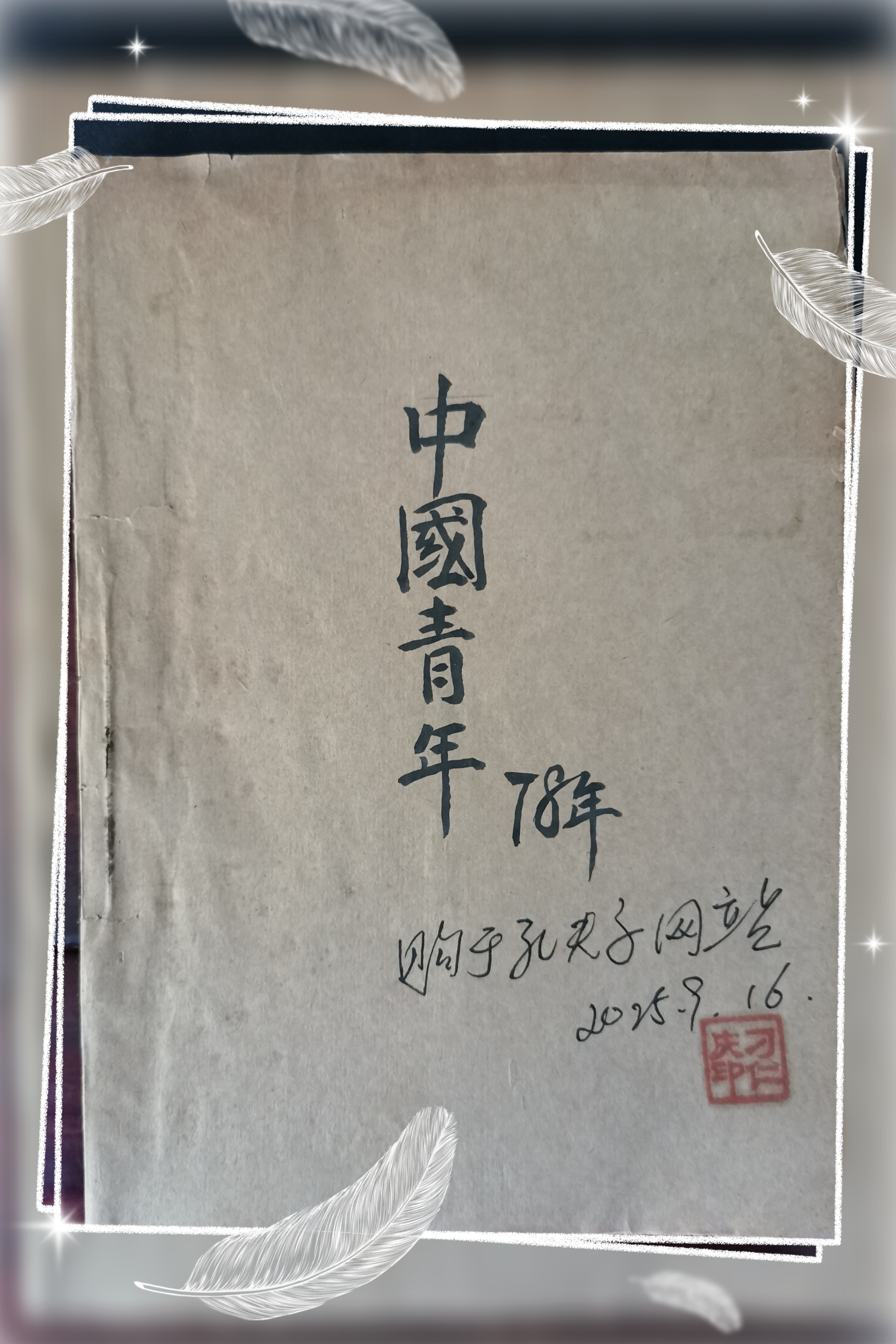
有時候我會想,是不是記錯年度了,是否會刊登在1980年的《中國青年》雜志上?仔細想想不可能,我記得很清楚,當年我是在團部彈藥庫站崗期間讀的這篇小說。我為什么記得這么準確呢?因為當年我們軍無線電密碼泄密,所有無線電臺都停訓兩個月,于是連隊就派我們去彈藥庫站崗,這個時候正好是1979年的春節期間,所以我就記住了這個時期。
其實,尋找這篇小說也就是一種情結,并非它寫得有多么完美,也不是說找不到它我就無法正常生活了,或者影響著我的創作什么的,不是,都不是,純粹是一種下意識地尋找。又是什么使我產生了這種“下意識”呢?細細想來,這篇小說應該是我文學創作風格形成的風向標。小說里面描寫碰杯的細節,不只是我在創作的時候會想起,在生活中每當喝酒的時候,都會在腦海中下意識地想起。特別是在我中年時期,喝酒的機會很多,想起的概率也就很高。想起這一情節的時候,就會想起這篇小說,想起這篇小說腦海中就會浮現這個細節。在這樣反復的相互作用下,促使我40多年來一直沒有放下尋找這篇小說的打算。
最近幾天,我為了準備創作《于無聲處》四部曲的第三部《紅色行動》,在孔夫子舊書網上搜索1942年《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大事記。突然又想起了1979年的《中國青年》雜志,當然還先想起了這篇小說中的主人公丁香。于是我就輸入了“1979年《中國青年》雜志合訂本”字樣。瞬間出來了一個合訂本的照片,我頓時心里一熱,眼睛一亮,激動起來,迫不及待地點開一看,品相很好,且是用硬皮裝訂的,于是馬上下單。那時已經是深夜12點了,我卻格外興奮, 直到凌晨2點才睡著。
不久快遞來了,我迫不及待地打開快遞,取出雜志,立馬坐在沙發上,一期一期地進行翻找。我戴上老花鏡,在每一期的目錄上尋找“丁香”二字。從第1期尋找到第12期竟然沒找到。這時,我失望的心無法形容。我納悶了,難道真的是我記錯了,它不是1979年發表的?我又把《中國青年》1978年那4期找出來,認真地翻找也沒有找到。這就怪了,難道是我真的記錯了日期?不會的。我在部隊近8年,在團彈藥庫站崗也就那一次。因為1979年春節是在彈藥庫過的,所以印象很深。由于我是在彈藥庫站崗期間看的這篇小說,那么絕對不會是1980年發表的。關于這篇小說,我牢牢地記住了四個要素:一是在《中國青年》雜志上發表的;二是在1979年春節期間閱讀的;三是那個酒杯交融的細節;四是主人公的名字叫丁香。

我查了查1979年全年的《中國青年》,上面總共刊登了5篇短篇小說,我決定把這5篇短篇小說都看一看,可能會有所收獲。當我翻開第2期里的小說《感情》時,看了兩眼就激動起來。原來我把這篇小說的題目記錯了,一直以為它叫《丁香》,其實它叫《感情》。作者是北京工藝美術工廠青年女工劉樹華。提起劉樹華,我隱隱約約地記得北京有個女作家叫劉樹華,難道是她?于是我馬上在百度上搜“劉樹華”,果然是她。搜索出來的內容是:劉樹華,漢族。出生于山東省濟南市,籍貫山東省蓬萊市。中共黨員。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作家班,系中央文學講習所第五期學員。1969年畢業于北京女子三中,后到吉林省白城市大安縣插隊,1976年回京進入北京市工藝美術廠工作,先后在黨委辦公室、組織人事科任職。具有政工師及助理經濟師職稱。中國工藝美術協會會員。1979年開始發表作品,1980年加入北京作家協會。先后在《人民文學》《北京文學》《中國青年》等刊物上發表作品,著有《感情》《花絲龍的命運》《吉他的朋友》《黃房子門上的鐘》等短篇小說及中篇小說。

看了劉樹華老師的基本情況后,我突然想起了當年轟動一時的“史鐵生老師與其他作家合作創作小說”故事。
?1985年在北京市雍和宮大街26號,六位作家通過每周聚餐吃火鍋的形式開展文學實驗:每人根據自身特質設定角色,采用循環接龍方式推進故事,創作全程未設大綱,僅通過突發事件串聯情節。這種集體創作模式打破當時個人寫作常規,體現了20世紀80年代作家群體對社會變革的思考記錄。
內容梗概:主人公舒展在插隊期間因腰椎傷病導致下肢癱瘓,返城后接手虧損的街道五金廠,通過技術創新扭虧為盈引發媒體關注。面對記者報道引發的爭議,他選擇堅守“用心靈走路”的信念,拒絕將事跡包裝成勵志典型,轉而將工廠利潤用于改善殘疾人福利。其間他與護士柳瑩突破世俗觀念的愛情抉擇,成為展現20世紀80年代價值觀變遷的重要線索。
這部小說叫《男人、女人、殘疾人》,由史鐵生、陳放、劉樹生、甘鐵生、劉樹華、曉劍六位作家采用循環接龍形式集體創作。書稿完成后曾向多家出版社投稿未果,直至2013年經武漢大學出版社編輯張璇發掘才重啟出版流程。該書定稿于史鐵生逝世三周年紀念日(2013年12月31日)前夕,成為史鐵生與陳放(2005年逝世)的遺作合集。曉劍作為原始手稿保存者,首次披露創作期間作家們擠在12平方米房間內寫作的歷史細節。其稿費全部捐贈給史鐵生、陳放兩位已故作家的遺孀,成為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罕見的集體創作實驗范本。
劉樹華老師參與了這本書的創作。
小說《感情》之所以讓我40多年忘不掉,原來是出自大家之手。小說《感情》是劉樹華老師的早期作品,那個時候她還在北京市工藝美術廠工作。1980年她就加入了北京市作家協會。她是北京大學中文系作家班的高才生,小說《感情》創作時起步之高,這就不奇怪了。能讓我掛念40多年也是很自然的事兒。
收到《中國青年》合訂本后,我又認真地閱讀了讓我牽掛40多年的小說《感情》,終于看清了它的全貌。
郭爺爺對丁香是有恩的。
很小的時候,丁香就和郭爺爺住一個院子。他是位受人尊敬的醫學教授。丁香的父母也是學醫的,經常恭敬地向他請教各種問題。那時候,郭爺爺鼻梁上架一副金邊眼鏡,頭發稀疏卻梳得整齊,白色漿領的襯衫束在筆挺的西褲里。丁香看著他令人尊敬的外表,心里就想:他一定是知識最淵博的人。
院子中間有一個洋灰砌的養魚池,丁香常常趴在邊上看池里的大金魚。池邊有棵丁香樹,郭爺爺常坐在樹下的藤椅上讀書。丁香聞見花香,就能想起他專注的神態,永遠像個用功的小學生。逢年過節,郭爺爺總要帶她去買小魚苗,還總高興地叫:“小丁香,快來,這魚苗兒多么好看!”因為郭爺爺喜歡丁香,爸爸和媽媽對郭爺爺說:“把小丁香送給您當孫女吧!”于是,丁香就親熱地往郭爺爺的懷里偎……
可是到了那個特殊的年代,小丁香對爺爺卻舉起了皮帶……
那個特殊年代結束后,丁香和眾多天真美麗的少女一樣,進行了反思:我們的思想觀念曾受到一些政治流氓的強奸,留下了無窮的恥辱。今后是痛不欲生,還是“放蕩”下去?然而,歷史總是更多地把真、善、美留下。就是在這種淘汰下,歷史前進了。
丁香痛苦一陣子后,她沒有“放蕩”下去。不久,丁香考上大學了,她收到報喜的信件(錄取通知書),并沒有十分高興,而是深深地陷入了自責和后悔中。因為此時她童年時期最親愛的、在那個“特殊時期”她傷害得最深的、后期在生活中關心、思想上指導、學習上幫助的郭爺爺已經去世了。
她對郭爺爺的傷害不是一般的傷害,而是致命的。小說中寫道:
在革命和感情之間,我帶著矛盾的心情選擇了“革命”。我被浪潮卷進深淵,和他們一樣,對著“反動科學權威”舉起了寬皮帶……
皮帶抽在爺爺身上,抽碎了我們之間的感情。爺爺當時勃然大怒,但看著我時,眼光卻茫然若失。那眼光使我恐懼、痛苦,不得不用強烈的“無產階級感情”來壯膽。當時革命道理就是那么簡單:我們真誠地崇拜偉人,捍衛上級,熱愛國家。除此之外,還明白什么,理解什么?
丁香樹上的花敗落了,爸爸、媽媽的百般勸說和責罵,都成了我革命的“阻力”。我和郭爺爺的矛盾,不,不是矛盾,沒有矛盾,是關系,親密的關系,就這樣轉化了。
一切都在變,風俗變了,習慣變了,人情變了。我,當然也要變,必須變。
生活就在無數對“敵我矛盾”中急劇推進:我天天造反,他天天勞改。在這種混亂中,常常牽動我心弦的,就是常在我眼前晃動的,爺爺頭上飄散的銀發……
丁香在懺悔中記起了哲人說過的話:人們在批判社會的時候,卻往往忘記了自己的責任,這責任,就是一個孩子咬在母親乳房上帶血的牙痕。
丁香決定拿著大學錄取通知書,到郭爺爺的墓地向他告別。路上,丁香還在回憶往事:后來那些日子里,郭爺爺每天掃街,要掃幾條胡同,任務很繁重。丁香每天上學時,總看到他佝僂的身影。金色的陽光沐浴著房屋、街道和他憔悴的面容。他站在那里若有所思,呆呆地盯著丁香,顯得那么蒼老,身子都彎了。郭爺爺發現丁香也盯著他,一時很慌亂,竟沖丁香笑了笑,他對丁香說:“走吧,好好上學,晚上見!”可看著丁香狐疑的眼神,他忽然醒悟似的大驚失色,匆忙又低下頭,顫巍巍地掃起街來。
那個瘋狂的年代結束以后,丁香又回到了郭爺爺的身邊。郭爺爺不但沒有因為丁香用皮帶抽打過他而恨她,反而和過去一樣,還是那樣地喜歡她,幫助她。郭爺爺越是這樣,丁香越感覺內疚,她對郭爺爺說:“我可是用皮帶抽打過您啊!”郭爺爺哈哈一笑說:“你真是個孩子啊,在我的記憶中,舉皮帶的從來不是你們,而是毒害你們思想的反動勢力。不要再亂想過去這些事了,專心下來學知識,為即將到來的新生活做準備啊!”此時,小說中寫道:
我胸口像塞了一個大蜘蛛網。”我似乎能感到而且能看到,在網的那頭,蜘蛛還在辛勤忙碌地把肚里的絲經緯延展地拉扯著,羅織得那么有規律。每個網眼都是一扇窗戶,每扇窗戶都通向遼闊的天空,就像爺爺那高潔的心靈。
我跟著爺爺舉起了酒杯……
酒漿濺灑出來,酒滴交融,又落在杯中,帶著馨香流進心田,在心底燃燒起感情的火焰……
就是這一段描寫,讓我記住了40多年。也就是這個碰杯的細節,讓我偷師借鑒了半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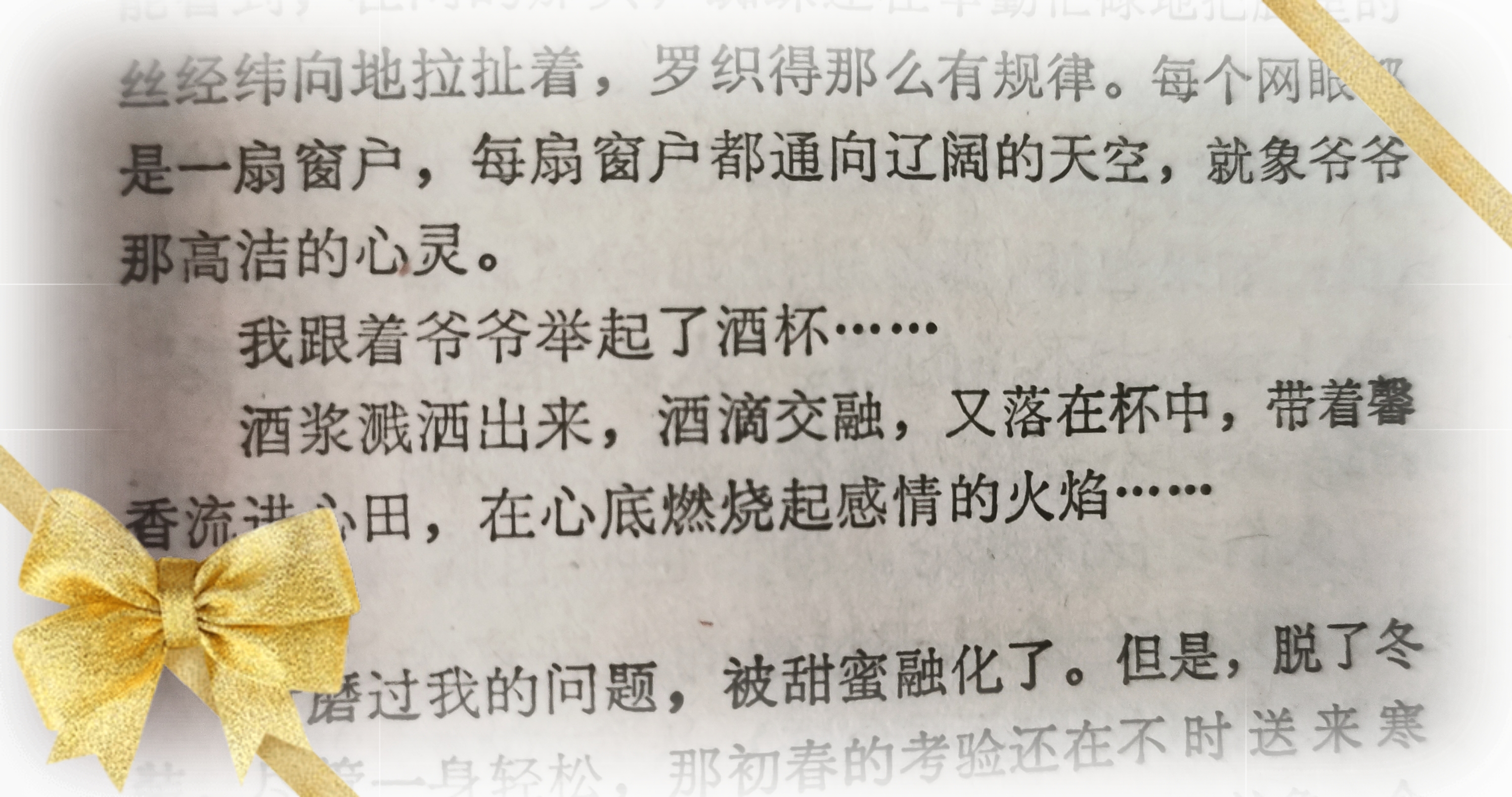
丁香來到郭爺爺的墓前,墓旁有棵小丁香樹已經開花了。丁香壓抑著涌上眼眶的淚水,撫摸著樹干想:他為我做過那么多好事,而我為郭爺爺做過些什么呢?如果我幫助他到處奔走要求工作;如果我在病床前精心護理他,在他心靈痛苦時陪伴他,跟他和“權勢”們爭辯真偽;如果我在他停發工資時接濟過他;那么,他的生活……可這些,卻沒有,一件也沒有!倒是在他重新工作以后,我和許多年輕人一樣,接受著他對我們的愛撫和教育:他幫助我們補習功課,鼓勵我們下決心為新生活做準備。正是這樣,才有了今天這樣的入學通知書。這是一筆多么不等價的心靈交易呀!代價就是他那顆破碎的心……丁香想到這兒,抱住郭爺爺的墓碑,放松地痛哭起來。
墓碑像郭爺爺的身軀,“溫暖”著丁香,丁香感覺她是在緊緊地抱著爺爺,這是從未有過的思想體驗。丁香和郭爺爺成了兩股巖漿,正隨著爆發的火山噴射著,那個折磨丁香的問題,折磨兩代人的問題,終于被這場思想體驗取代了!咬媽媽乳房的孩子長大了……
丁香撫摸著墓碑,她突然暗暗地下定決心,要干一件使丁香心靈感到慰藉的事。這件事就是她要在墓碑上刻上這樣一段文字:“一個珍愛美好感情的人!孫女丁香敬刻。”
丁香的嘴角感到一陣咸味,抹了一下,是淌下來的眼淚。丁香看了看墓碑,又看了看丁香樹,心里像藍天一樣潔凈:我完成了一件大事,我拿出入學通知書,又看到了爺爺青春的身影。我將把心中的感情永遠埋在最深處,任何時候不再玷污它。從此,一切的一切都為爺爺所說的“明天”,一切的一切都為過去的悲痛不再回到我們中間!
天那樣高,云那樣白,路那樣寬。道路那頭仿佛在向丁香招手,在甜蜜地等待著她。丁香靜靜地離去,悄悄地走了!她想:爺爺,等到明天,再到墓前喚醒您,送一束您最喜歡的丁香花。
劉樹華寫的這篇小說《感情》,應該歸類為“傷痕文學”。而且與傷痕文學的發源人盧新華的小說《傷痕》有點相似。現在看來它是一篇很普通的小說。然而是什么力量能讓我尋找40多年呢?尋找丁香,成了我多年的渴望。我讀的書稱得上是汗牛充棟,但好多書讀過也就印象不深了,里邊的人物、故事和細節我不可能都記住。一個細節和人物能讓我記著40多年的微乎其微,唯獨這篇《感情》讓我記住了。這是為什么呢?原因就是,大部分小說當我想起它的時候,我都能重新找出來進行二次閱讀。而《感情》不行,我每每想起它卻無法找到它,越是無法找到它,尋找它的愿望就愈加強烈。尋找它的欲望促使我無法忘卻它,愈是無法忘掉它,愈是下決心一定要得到它。
這么多年,尋找丁香成了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內容。今天,我終于尋找到了丁香,我如釋重負。在未來的日子里,一旦沒有了尋找,是不是缺少點什么呢?
讀書人身上會發生很多怪事情,尋找丁香這件事,也應該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了。

(刁仁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南陽市作協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