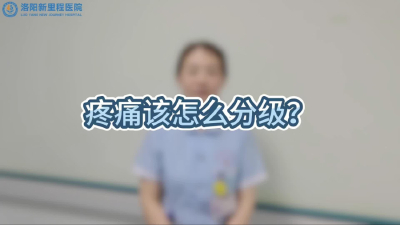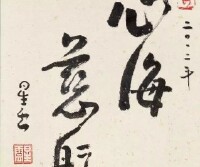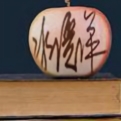鹽的淚,愛的碑——讀《愛與痛的起點》
月光初落時,總以為生命是單薄的紙,一面寫著愛,一面刻著痛。直到在某個不期而遇的詞語里讀到自己的倒影,才發(fā)現(xiàn)愛與痛原是同一道河流的兩岸,中間奔涌的,是血脈里不會冷卻的溫度。
這首詩從第一行就種下了命定的密碼——“你是愛/也是痛的起點”。這并非二元對立,而是生命的完整敘事。新生命的誕生總伴隨著撕裂與劇痛,可那“門口的照壁都光亮亮的”,仿佛整個宇宙都在為這場神圣的抵達整肅儀容。最動人的是那個“未出世即大鬧龍宮”的意象——孩子尚未睜開眼睛,就已經(jīng)在焦急地尋找母親的懷抱。這種原始的、近乎本能的親緣渴求,讓生命的起點染上了宿命的溫暖。
然而,詩的筆鋒如時間本身一樣無情流轉(zhuǎn)。“最疼愛的那個人/一聲不響,把自己嵌進了/黑白相框。”這里沒有渲染悲傷的辭藻,只是平靜地陳述一種永恒的缺席。可正是這種平靜,讓后來的“嘴抽動著”有了千鈞之力——那是尚未學會完整哀悼的軀體,用最原始的顫動來承接這巨大的失去。
“雙手依舊攥緊漏走的溫度”,這是全詩最溫柔的抵抗。溫度會漏走,如同沙粒穿過指縫,可攥緊的動作本身,已成為一種永恒的姿勢。玻璃窗上半輪殘月的意象,冷得恰到好處——那不是絕望的冰冷,而是清醒的、必須面對的離別溫度。
真正的詩眼在最后的玫瑰。紅色與白色的分野,不是生與死的隔閡,而是一種延續(xù)的儀式。“紅的留我,白的將你依偎”,這里沒有天人永隔的悲嘆,只有顏色不同的相伴。風如刀,瓣瓣飄飛,這飄零不是結(jié)束,而是另一種形態(tài)的存在——就像鹽粒會硌手,卻也證明了淚水曾經(jīng)真實地流過。
通讀全詩,看不見刻意營造的哀傷,只有時間沉淀后的清明。作者似乎在說:最深的愛里必然包含最真的痛,而最痛的失去里,也埋藏著最純粹的愛。那些“結(jié)晶的淚”和“硌手的鹽粒”,原是同一物質(zhì)的不同形態(tài)——就像記憶與遺忘,擁有與失去,相聚與別離。
當玫瑰花瓣在風中飄散,我們終于明白:愛不是對抗時間的盾牌,而是與時間和解的方式。每一片飛散的花瓣都在說——我曾在枝頭燦爛過,而此刻的飄落,不過是在完成另一段旅程。
這或許就是詩的初衷:不為銘記,不為遺忘,只為誠實地見證——見證愛如何從疼痛中誕生,又如何穿越疼痛,成為生命本身。
——張野鬼2025.12.19日夜于廣州白云機場
回復 張野鬼(云南·鎮(zhèn)雄) 辛苦啦,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