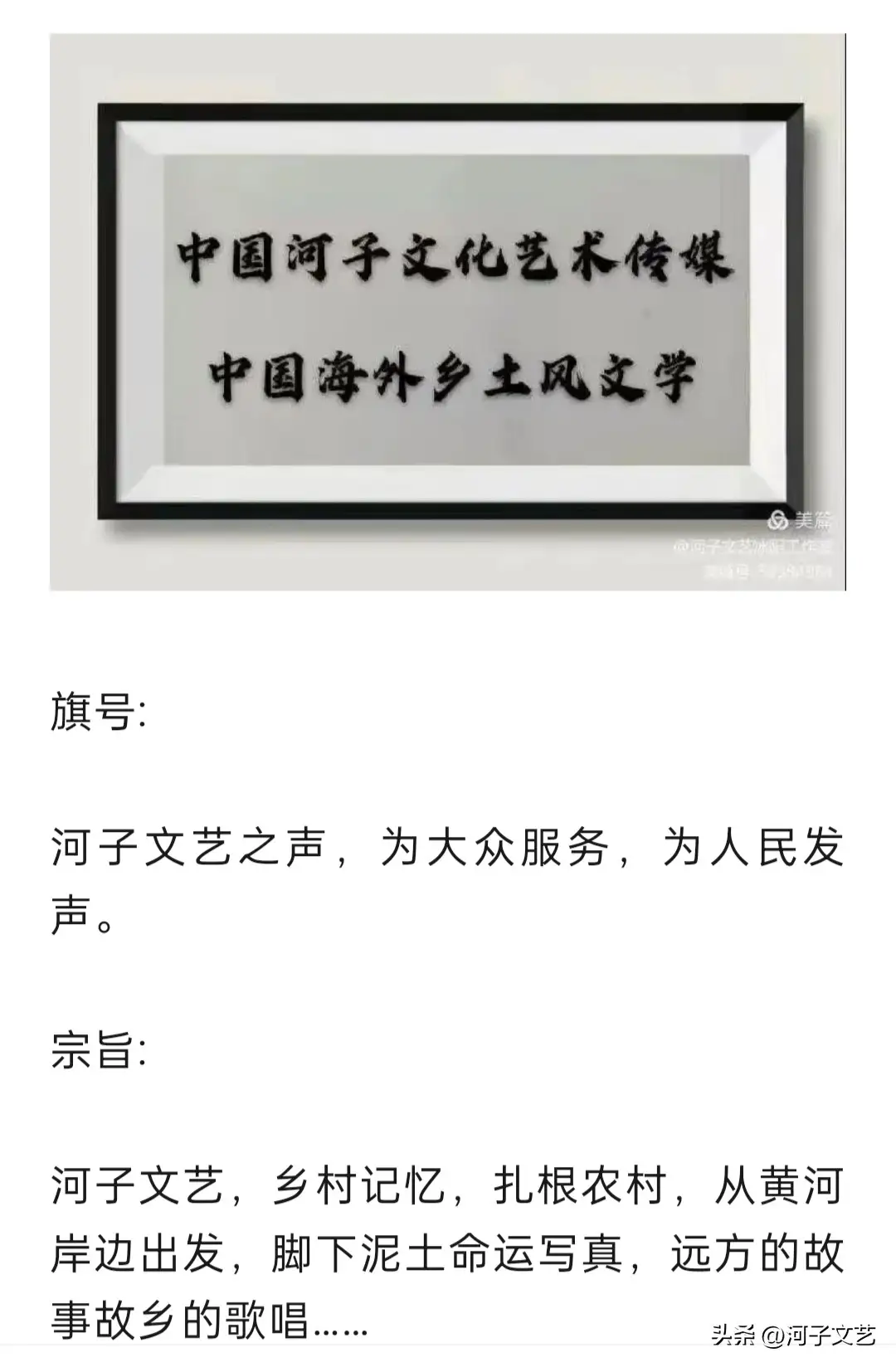2025第一場雪,北疆與魯地的雪色重逢(散文)
文/冰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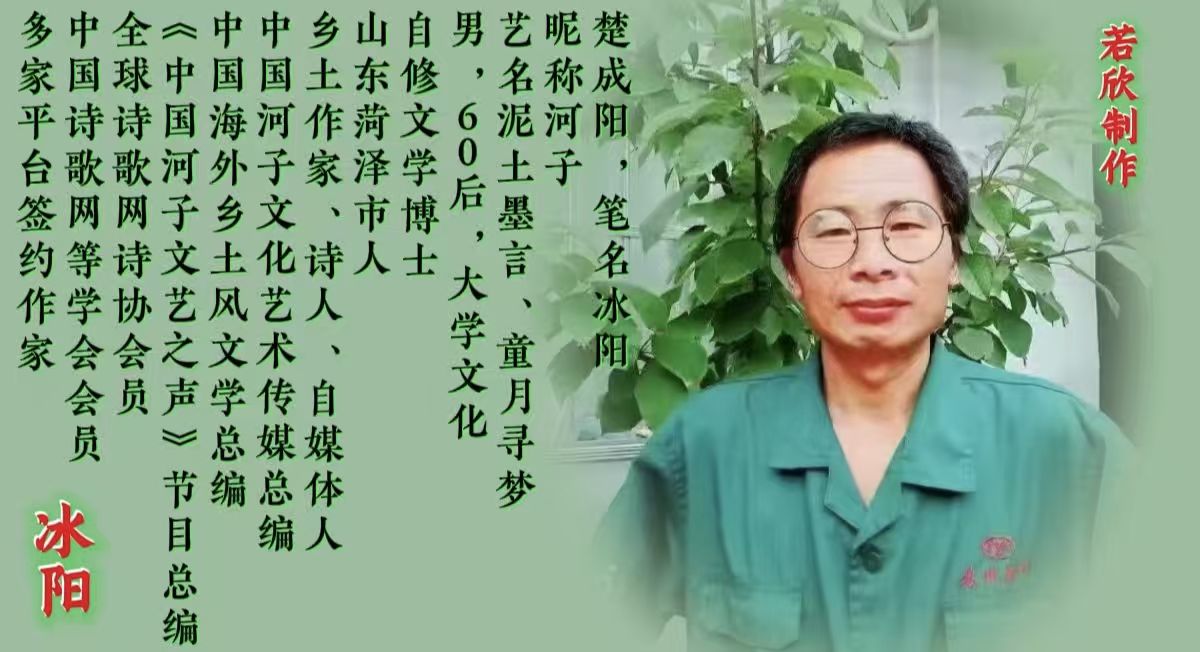
2025年的第一場雪,像是被風牽著的白綢,先掠過天山北麓的烏魯木齊,又飄向黃河下游的菏澤牡丹區。當好友從烏魯木齊發來雪覆松柏的照片時,我指尖劃過屏幕上的銀白,忽然就跌進了1997年春天的北疆記憶里——那年我踏過奎屯的雪融土路,摸過瑪納斯河畔還掛著冰碴的柳枝,也在烏魯木齊的街頭,見過春雪裹著沙塵落下來的模樣。而此刻,菏澤黃河岸邊的雪正簌簌落在衰草上,兩種雪色隔著三千里山河相遇,把時光揉成了一團溫涼的白。

烏魯木齊的雪,從來都帶著北疆獨有的磅礴氣。好友發來的兩張照片里,松柏被雪裹得嚴實,深綠的針葉從厚厚的雪層里探出來,像被白棉絮裹住的墨玉簪。那些松柏生在城市的邊角,不是精心修剪的園林樹,而是野氣十足的北疆原生松,枝干遒勁地向天空伸展,雪落在枝椏上,不是輕飄飄的覆蓋,而是沉甸甸的堆疊,雪團墜著松枝微微彎曲,卻又始終不肯折斷,像北疆人骨子里的堅韌。
我想起1997年的春天,第一次到烏魯木齊時,也遇上了一場遲來的雪。那時的烏魯木齊,街道兩旁的白楊樹還沒抽芽,光禿禿的枝椏上積著雪,風一吹,雪沫子就順著街道滾,像是撒了一把碎銀。我坐著車從市區往奎屯走,窗外是戈壁與農田交錯的景象,雪落在戈壁上,沒入枯黃的梭梭草里,只留下淺淺的白痕;落在麥田里,卻給凍得硬邦邦的土地蓋了層薄被,老農站在田埂上抽煙,說這春雪是“麥蓋三層被,枕著饅頭睡”,北疆的雪,連帶著農人的期盼,都帶著一股子豪爽。
到了奎屯,雪下得更密了。奎屯的雪不像烏魯木齊那般帶著城市的煙火氣,而是裹著戈壁的風沙,打在臉上涼絲絲的。我踩著沒到腳踝的雪,走到奎屯河邊,河面還結著厚冰,冰面上覆著一層雪,遠處的雪山在霧里若隱若現。當地的朋友說,奎屯的雪來得猛,去得也快,不出三天,河邊的雪就會融成水,順著河道流進瑪納斯河。后來去瑪納斯,果然見著了融雪后的河水,渾黃的水流裹著碎冰,嘩啦啦地淌,岸邊的柳樹上掛著冰棱,陽光一照,折射出細碎的光,那是北疆的雪從固態到液態的蛻變,粗糲里藏著溫柔。
如今再看好友發來的烏魯木齊雪景,松柏上的雪比1997年的春雪更厚,卻依舊是熟悉的北疆雪色。那些松柏的枝葉間,雪積得像蓬松的棉花糖,偶爾有麻雀落在枝上,抖落一片雪霧,旋即又飛走,留下枝椏在風里輕輕晃動。烏魯木齊的冬天,雪是常客,卻每次都能給人新的震撼——它不像江南的雪那般嬌柔,落地即化,而是執著地停留在枝頭、屋頂、街道,把整座城市裹成銀裝素裹的世界,連空氣里都飄著雪的清冽味,吸一口,涼到肺腑里,卻又讓人覺得神清氣爽。

而菏澤牡丹區黃河岸邊的雪,是另一番溫柔模樣。第三張照片里,夜色籠罩著河岸,雪薄薄地覆在地面上,沒有北疆雪的厚重,卻帶著黃河的溫潤。我站在黃河大堤上,伸手接住一片雪花,它輕飄飄地落在掌心,沒等我看清形狀,就化成了一滴水珠,順著指縫滑落。黃河岸邊的雪,像是被黃河的水汽浸潤過,雪粒細碎如鹽,落在衰草上,給枯黃的草莖裹了層白霜;落在堤岸的泥土上,融成淺淺的濕痕,混著黃河的泥土氣息,聞起來有股子煙火味。
這是菏澤2025年的第一場雪,來得比往年稍晚些。黃河在夜色里沉默地流淌,水面上泛著暗沉沉的光,雪落在河面上,瞬間就消失了,像是被黃河的浪濤吞了進去。大堤旁的楊樹林,葉子早就落盡了,光禿禿的枝椏上積著薄薄的雪,像給樹枝描了道白邊。偶爾有夜鳥從林子里飛起,翅膀扇動的風,抖落枝上的雪,雪沫子在夜色里飄著,像是撒了一把星光。
我蹲下身,摸了摸堤岸的雪,底下的泥土還是軟的,帶著黃河灘獨有的濕軟。牡丹區的雪,從來都和黃河綁在一起,它沒有北疆雪的凜冽,卻有著中原大地的溫和。想起小時候在黃河岸邊玩雪,堆的雪人總是站不了多久,就被黃河的風刮得歪歪扭扭,雪也融得快,到了中午,雪水就順著大堤的斜坡流進黃河,像是給黃河添了一勺清甜。如今再看這河岸的雪,依舊是兒時的模樣,細碎、溫柔,帶著黃河的氣息,讓人心里暖融融的。

三千里的距離,烏魯木齊的雪還在松柏枝上堆積,菏澤的雪卻已在黃河岸邊悄悄融化。兩種雪色,一種磅礴,一種溫婉,卻都讓我想起了時光里的那些瞬間——1997年北疆春雪里的戈壁、麥田、河流,還有如今黃河岸邊的夜色、衰草、大堤。2025年的第一場雪,像是一條白絲帶,一頭系著北疆的蒼勁,一頭系著魯地的溫婉,也把我記憶里的1997和當下的2025,系在了一起。
我對著烏魯木齊的雪景照片,想起1997年在烏魯木齊街頭吃的烤包子,外皮焦脆,內餡鮮香,就著雪水喝的磚茶,暖到了胃里;又看向黃河岸邊的雪,想起家里煮的紅薯粥,甜絲絲的,配著剛烙的蔥油餅,是魯地雪天里最踏實的溫暖。北疆的雪,讓我記起年少時的闖蕩與新奇;魯地的雪,讓我感受到歸家后的安穩與溫柔。
雪還在落,烏魯木齊的松柏依舊頂著厚厚的雪團,菏澤黃河岸邊的雪還在細碎地飄。2025年的第一場雪,不僅是天地間的一場盛景,更是我與舊時光的一次重逢。那些散落在奎屯、瑪納斯、烏魯木齊的記憶,被這場雪喚醒,又與菏澤黃河岸邊的雪色交融,匯成了心底最柔軟的念想。原來雪是有記憶的,它落在北疆的土地上,也落在魯地的黃河邊,更落在我走過的時光里,歲歲年年,不曾消散。
當晨光熹微時,烏魯木齊的雪會被陽光照得發亮,松柏上的雪團會慢慢融化,滴落在地上,匯成小小的水洼;菏澤黃河岸邊的雪,也會在朝陽里消融,堤岸的泥土會變得更加濕潤,等著來年春天牡丹的綻放。而我會把這兩場雪的模樣,妥帖地收進心底,就像收藏起1997年北疆的春雪,收藏起黃河岸邊的冬日溫柔,讓2025年的第一場雪,成為時光里又一個溫暖的印記。
2025年12月12日作于河子書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