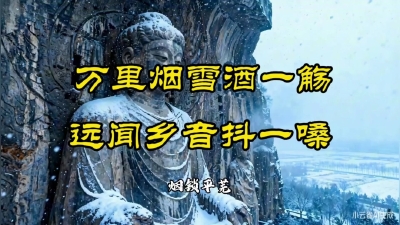我的家鄉話
豫東平原的風,總捎著一股子帶著土腥氣的鄉音,那是刻在我骨血里的家鄉話,是村里大喇叭的晨鐘撞開的第一縷炊煙,是黑河水漫過田埂時的細碎呢喃,是老柳樹枝頭上的蟬鳴裹著的人間煙火。
它不是書里印著的平仄,也不是電臺里字正腔圓的播音。它是黑河邊老柳樹底下,大爺們搖著蒲扇嘮嗑時,一句拉長了調子的“中不中”,尾音里裹著柳絮香,飄得滿街都是;是黑河岸邊,嬸子們踮著腳站在村頭喊娃回家吃飯時,一聲帶著急腔的“俺孩兒嘞”,驚飛了河灘上啄食的白鷺,也驚落了柳梢頭的斜陽;是田埂上,漢子們扛著鋤頭下地時,一句豁亮的“走,薅草去”,震落了草葉上的露珠,也震醒了沉睡的莊稼苗。
這鄉音,裹著麥香。小時候蹲在打麥場的石磙旁,看父親光著膀子揚場,金黃的麥粒兒在風里劃出一道道弧線,他嘴里念叨著“芒種忙,麥上場,收麥如救火,龍口奪食忙”,那帶著豫東土味兒的諺語,就跟著麥粒兒一起,滾進了我的耳朵里,落進了曬得發燙的麥秸垛里。他說“吃罷端午粽,才把棉衣送”,說“春施千擔肥,秋收萬擔糧”,那些樸素的道理,被家鄉話揉得軟軟的,像灶臺上剛蒸好的白面饃,咬一口,麥香混著煙火氣,從舌尖暖到心窩,連打個嗝兒,都是麥浪翻滾的味道。
這鄉音,浸著軍魂。三十年前,我背著印著紅五角星的行囊離開家,村口的大喇叭里,村支書扯著家鄉話的嗓子喊“當兵光榮,保家衛國,咱村的娃,個個都是好樣的”,那鏗鏘的鄉音,是鄉親們擠在村口的目送,是奶奶偷偷抹淚時塞給我的煮雞蛋,也是我胸膛里滾燙的熱血。新兵連的夜里,想家想得睡不著,隔壁鋪的同鄉悄悄湊過來,用帶著鄉音的耳語說“甭想家,咱當兵的,走到哪兒都是家”,一句話,就把眼眶里打轉的淚,硬生生憋了回去。拉練時腳底磨出了泡,咬著牙往前走,耳邊總響著那句鄉音:“咱豫東的娃,骨頭硬!”——家鄉話是漂泊在外的根,不管走多遠,只要聽見那熟悉的腔調,就知道,自己不是無根的浮萍,身后有整片豫東平原的守望。
這鄉音,藏著鄉愁。后來我在鄭州扎根,這座城的方言里,也有豫東話的影子,卻總少了幾分黑河水的清冽,少了幾分黑河河畔老柳樹的陰涼,少了幾分打麥場石磙碾過的厚重。偶爾在菜市場聽見一句“這白菜咋賣嘞,恁貴”,扭頭一看,是操著鄉音的老鄉,臉上溝壑里的笑意,像極了老家曬秋時的玉米穗。相視一笑,不用多說,那一句家鄉話,就把兩個異鄉人的距離,拉得很近很近,近到能聞見彼此身上那股子洗不掉的土腥氣,近到能看見老家的炊煙在心頭裊裊升起。后來我在小區里開了個小菜攤,擺上老家帶來的芝麻葉、紅薯干,吆喝聲里不自覺就帶出鄉音,“嘗嘗唄,咱豫東的土特產,味兒正嘞”,竟引來不少老鄉駐足,一來二去,攤位成了鄉音的聚集地,家長里短的鄉音混著煙火氣,把鄭州的日子,也過得有了老家的溫度。
我的家鄉話,是刻在舌尖的胎記,是埋在心底的鄉愁。它沒有華麗的辭藻,卻有著最動人的力量——它能把千里之外的故鄉,拉到耳邊;能把散落在歲月里的記憶,串成一串珍珠;能讓我在風里雨里走了半生,一回頭,還能看見那個蹲在打麥場的孩子,聽見那句熟悉的鄉音,在豫東平原的上空,伴著老柳樹枝頭的蟬鳴,伴著黑河水的流淌,久久回蕩,從未消散。
我的家鄉話
文/劉天龍
2025-12-16 22:43來源:冬天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