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屆拾壹月詩歌獎作品展
新銳詩人獎獲得者——劉蕭

劉蕭,男,出生于1989年,湖北十堰人,現就讀于山東大學威海校區當代文學博士,主要從事當代詩歌研究,著有詩文集《日子的新娘》等,獲第三屆拾壹月詩社新銳詩人獎。
1.星星的遺囑
黑洞已經在召喚我。
由虛無所構成的軌道開始崩潰
核心之彩蛋向我低語:
那便是我們要去的地方
——力的終結,一切光的墓地。
再給它們最后一個黃昏:
陸地,水域
進化中的生命,
正在萌芽的語言,
和即將誕生的諸神。
這一切都將結束。
黃金時代尚未開始,
黑鐵時代也不會到來。
不要試圖辨認
在發光之前,我將消失。
2013年4月
2.生日贊歌
——為Z十六歲生日而做
這一天已經過去或者尚未到來
少女,那就讓每一天都成為你的節日
昨天正含著青澀的淚水同你告別,
而明天就是春天。在這冰雪消融之日
愿你的肉體像樹愿你的靈魂像風。
愛情的聲音也隱約開始向你發出召喚:
在那風雨飄搖的夏日之巔
一道閃電,
落進大地幽暗的私處。
我們曾同樣赤裸,共用一彎命運的新月
(而滿月之夜,園丁注定要被花朵摧
毀)
我祝福你正如我也曾被祝福
愿這祝福能穿過時間的黑暗
抵達兩顆星辰之間,你被遺忘的吊床:
愿花朵盛開,并在凋謝之前給它以贊美
愿你的微笑成為所有淚水的故鄉
愿你能獲得幸福
愿大地能成為愛人們的家園
愿一切戰爭,僅僅發生在我靈魂的內部
2014年7月
3.晨歌
我們總會擁有這樣一個早晨,
它包含了所有的早晨
(正如你包含了所有的女孩
那些我遇到過的,夢見過的
甚至尚未存在的)
我們迎著光醒來,在同一張床上
摻著少許殘留的睡意
我會毫無緣由的向你講起
它們其中的一個:
我小的時候老家那邊蓋房子
不論是蓋什么樣的房子
總少不了它們--那些樹
它們在深山被伐倒,用卡車運回
碼放在院子里靠墻邊。
那時八歲或者九歲的我
站在一個五月或者六月的晨光中
穿著短袖短褲,看著大人們怎樣首先
把那些樹的皮都剝下,露出潔白而
潮濕的樹干(就像你現在這樣),
然后用長鋸從中剖開。
地上鋪滿一層厚厚的鋸末,像雪
純潔的香氣驚醒角落里沉睡的蝴蝶。
他們汗衫濕透,晶瑩的汗珠
從他們光著的膀子上滴落
木材會被刨光,按長短、厚薄、寬窄
截成各式各樣的尺寸,最后變成
房梁,椽柱,桌椅和門窗
還有一些其余的小家具。
一股隱秘難言的悸動從我身上涌起
當我看見那一雙雙大手
揮舞著錘子,和著起伏的號子
將一枚枚銀色閃光的釘子
釘入木頭光滑無暇的軀體。
在一陣難以抑制的暈眩中
我仿佛看見,我們躺在晨光里
而一把無限溫柔的錘子
正一下,一下,一下
將我們釘入這個世界。
2015年5月

4.冬天的魯濱遜
這是你一個人的冬天
眾水環繞。這兒并非熱帶
被棄置在世紀的孤島上
已經很多年。還很早,
霜的冷香像箭從黎明射出
暗暗穿過樹籬;
洞穴的墻壁掠過一陣火光
那是野蠻人在狩獵,傳來
吶喊聲和號角,又漸漸變遠……
真是個艱難的時節。
沒有星期五,
有時為了活下去,你不得不
成為他們中的一員;
然而,無論怎樣,你該跪下來祈禱
不是每個人,當他的
生命船傾覆于夢的風暴
都能獲得這樣一個島嶼。
父親是對的,他的勸誡
卻抵不過你漂泊的本性。
想想最初的那些日子
作為唯一的幸存者的慶幸與絕望,
偶有船只路過,又聾又瞎
呼救的篝火在沙灘上
徒勞地焚燒,又熄滅。
但畢竟還有些東西
從那沉掉的墳墓里打撈上來:
槍支,火藥,一些工具
勉強可以活命的食糧
(包含少許的種子)
一本圣經,半瓶墨水
甚至還有一些朗姆酒。
接下來的是勘察,狩獵
和伐木。把自己安頓在
一種慣性中,一種煩忙的節奏里。
這些勤懇的勞作,是否真的
根植于生存的本義?
希望的禿鷲每天都會
和第一縷晨光一同前來,
啄食你一小片肝臟。
整整三個月,那株巨樹
被砍倒,去皮,曝干,
一點點被鑿空,慢慢
呈現出一艘船的樣子;
在午夜睡夢的激動中,
你幾乎看見自己,怎樣駛著它
穿過滔滔大浪,或是在
星光寧靜的夜下航行,
最終抵達一個燈火輝煌的港口!
你終于完成了。并在
變涼的汗水中清醒過來:
哦,這愚蠢的龐然大物。
能駕馭它的人尚未出生
或者早已死去。忘了它吧,
任它被風雨吹打,
在熾熱的光照下裂開,成為
蟲蟻食物或鳥獸的巢穴。
你必須重新審視這些
正變得面目猙獰的風景。
在一天一天空洞的寂靜中
它們長出獠牙和利爪,
總有一天會成為野獸
無情的將你撕碎,吞噬。
危險日益逼近,你開始學習
死者們留下的語言
重新為它們命名,并試著把自己
從一個囚徒變成領主。
經過五個個夏天和許多場風暴
在深秋的一場濃霧中,
你終于將厭倦和絕望
馴化成潮汐。幻覺之鳥
迷失在溫暖如火的南方
你把情欲的皮毛
在冬天冰冷的骨架上撐開,
盡管那手指間雅致的藝術
已經變得貧乏和麻木。
明天,又一個明天
筆記本上又多了道黑杠
瓶子里的墨水還剩最后一點。
以誰之名,該向誰核對
日子的差錯和疏漏?
時代已經破碎,察覺即宿命
突然一陣風,
意義之燈被吹滅。
你站起身,走出洞穴
看見黎明暗沉沉的大海
仍舊在寒冷的夜色中沉睡。
你已忘記,船最初沉沒的地方
仿佛那從未發生;
仿佛有隱約鐘聲
從一個看不見的深淵傳來
震蕩著這黑暗
是的,就是這個時刻。
那些被夢的浪濤卷走,漂泊于
陌生天空下的旅人,
正再次乘著夢回家。
2016年11月
5.新房間
窗外的積雪被煙花照亮,
大地,一片寒冷幽暗的水晶
酒的波浪微微搖晃著床。
這黑暗是新的——也是新的債務
書蜷縮在對面的書架上
打著輕鼾,這些嬌氣的客人
走了長長的路
它們比你更像是孤兒。
在第二十八個冬天,
一顆蔚藍行星上的褐色季節
這片由泥沙、木材、鋼鐵和血汗
所圍聚起來的空間
——屬于你。
午夜夢回,帶回來的
還有詞語的潰敗。
你們一同在夏日黎明出發,
空氣中釀著蜜
天空的剪影
從路旁的樹枝間緩緩飄墜。
車窗外的每處燈火都在鼓勵:
沒有什么遠方不能抵達……
另一個黎明,地平線上
翻涌的云筑一座城堡
迎接閃電的主人。
在南方小鎮,你第一次看見
陽光掠過教堂奶白色的尖頂
一個故事已經悄然發生。
健碩的狼狗在工廠后門狂吠
機器的轟鳴中,每張倦怠的面龐
背后都有一個嬰孩在沉睡。
你為它們寫下搖籃曲。
而一顆浸泡在化學藥水中的少女之心
依舊在怦然搏動!
這樂音的美你尚不能承受,
于是,最初的債務被欠下
晚霞在沉默中計算著利息。
在星期天的教堂你聽見布道——
有關“上帝的愚行”
孩子們在電子琴的伴奏中哭鬧,
贊美詩像一部外國電影的拙劣翻譯。
散場時人們領取洗粉,人字拖,毛
巾……
你領到一瓶醬油。
男孩們騎著摩托在逼仄的街上狂飆;
夜色中,少女被耶穌基督誘拐
一只美麗的豹子就這樣消失了,
你尚未抵達人生的中途
如今你已經抵達。
接近而立之年,卻依舊只能在
謊言的灌木叢中匍匐前進。
荒蕪的十年,二手的十年
——一個暴躁的孕婦
——一個幼稚的間諜
揮霍野獸,花朵和幻象,
在屏幕和路燈的瞪視下
和影子一起操練愚行。
總是入不敷出,寒磣的收入
尚不足償還利息,
三千個夜晚的月光和祈禱被透支殆盡。
在這新的枷鎖和新的牢房里,
淚水和溫情中摻混著權力的味道
已經很晚,你只想盡快結束這場訊問
和在書頁間筑巢的夜鶯,
一起進入一場遺忘的冬眠。
但你清楚,不管睡得多甜多死
總會有一個噩夢把你驚醒
讓你一躍而起,
狂奔在歲月不斷坍塌的洞穴
一邊活下去一邊埋葬。
2017年11月
6.鄉村婚禮
——獻給B
所有的允諾都已完成。陽光
在塵土和臘月的寒風中贊美
這片我們稱之為大地的星
越過山脊,越過那個沉睡的
女人積雪閃耀的腹部,無人處
影子領回了漫游者
離吉時還差片刻,如同進入
悠長夢幻前的片刻清醒
沒有什么夢幻,一個聲音輕輕地
提醒著你。沒有什么聲音
即將發生的一切都無比真實
正在發生的一切也是如此:
喜慶的鑼鼓和嗩吶充盈著山谷
枯褐的河床,脈搏微弱而平穩
一場初春的洪水已經在路上;
充氣拱門矗立在道路中間
像某個游樂場的入口
一張干凈的舊紅毯,順著木板搭成
的斜坡,鋪伸到那個臨時搭建的舞臺
煙花在白晝的空氣中嘯叫
進行最后的暖場
如散落在各處的珠子,人群
被習俗的麻線暫時重新串起
在路邊,在豬圈旁,在屋檐下:
久未謀面的朋友,熟人
只存在于族譜上的遠親
和許多未曾被覺察的缺席
嘈雜聲中的閑聊,寒暄,被一陣
可以預見的寂靜中斷――
那對花蕊已經出現在舞臺上
眾多面龐如花瓣般簇擁過來:
仍舊面朝黃土黝黑的臉
在城市寫字樓里被漂白的臉
被胃痛折磨的呻吟的臉
尚未從通宵的牌局里蘇醒的臉
皺如紙幣和含苞待放的臉
還有角落里那個,溫柔的瘋子的臉……
時辰到了,親愛的朋友們
今天我們來到這兒,來到這個
淺如水洼的山村,并非是為了
慶賀彼此的絕望
誰導演著這一切?是那個
留偏分、著紅色西裝的司儀?
他熟稔又漫不經心地走著流程
還要去鄰村趕下一場。
這是屬于土地和野獸的時辰――
溫柔一點,牽引著我們身后
看不見的線的那雙手;寬容一點
存在或者不存在的觀眾
原諒他們作為臨時演員的拙劣:
土洋結合的妝扮,僵硬的幸福表情
浮夸的誓言,幾乎是機械地
交換著紅酒杯、吻和鉆戒
還有關于財政權歸屬的老套橋段。
也不要用真愛和永恒將他們嘲笑
在甜蜜的虛假,神圣的滑稽背后
隱含著契約的真義。孩子們,姑且把他
們
當作你們幸福的榜樣吧,
在痛苦與平庸之外,你們會找到
一條屬于自己的路……
終于到了你們。在眾目睽睽的歡呼中
你們悄然對視,然后微微顫抖
不是因為寒冷也非因為幸福。
有些事注定會發生,比如厭倦
比如悔恨。在兩種后悔之間
你們已勇敢選擇其中一種
而有多少錯失愛情的人,依舊在
虛無面前,保持著貧困的清醒。
人群即將散去,但你們不會
一個空寂的房間已經在等待
在大地上某處。你們將走向它
一邊搬運石頭,一邊釀蜜;不要理會
那些關于如何優雅變老的謊言
準備好汗水、決心和眼淚
在繚繞于明天永恒的霧靄中
你們將一同歷經漂泊、疲憊和衰老
直到成為另一個故鄉
2018年12月

7.武漢哀歌
所有的霧都是同一場霧,我們進入霧的時間
灰燼中的玫瑰依舊年輕,隱沒入冬天的靜脈
麻木。痛楚。欲望的燈塔閃耀兩次
我們漂流,沉睡,在搖籃到墳墓間的波浪上
一只手攪動著這溫柔的混沌
這是誰的夢境?墜落和飛翔同時發生
午夜鋼鐵咆哮。一枚猩紅的月亮升起
幻覺的瘟疫在時代的肺葉筑巢
越過謊言的欄圈,故鄉的牧場羔羊遍地
飲下眼淚的杯盞,天空的慶典在繼續
詞語的血折射著大地之光
某一天某月的某個城市,我們尚未相愛便死去
2020年2月
8.三十歲的第一場雪
告別獨角獸,父親喊我起來看雪
午后三點。在異鄉一個臨時的家
桌上攤開的書如一艘靠岸的船
繞過這個比喻的轉角
我來到窗前,睡眼惺忪
看見雪從三十歲的天空落下
夢該醒了。我曾用青春的一半
來品嘗虛無和向語言求愛
這只是一個人的失敗
美麗的卓瑪永不會老去
母親煮好茶。雪帶著歉疚飄落
馬桶里傳來一陣未來的忙音
明亮而繽紛的沉默,籠罩著
這城市的癱瘓和我的而立之年
沒有遠方。為了抵達意志的邊境
許多人都深陷在此刻的雪中
進入一種命運為時尚早
回到愛的行列又顯得太遲
是建造自己的房屋的時候了
鵝毛和柳絮通過雪結成姐妹
而我孤獨如昨。回憶里升起
一顆南方的星星,帶來一小片夜
我知道我會幸福,如果我愿意
忍受生活的必要之惡
如果被雪遺忘,我能忍受更多
傾聽著時間和肉體空洞的回聲
我的手,再一次屈從于筆的戰栗
寫詩,一個既死又活的悖論:
穿過病毒的封鎖,一個間諜
披著雪,重新潛入虛無的國度
2021年3月
9.新年哀歌
親愛的,又是新的一年。霧尚未散去
這個冬天的骨頭是多么黑暗
伴隨著戰栗和遺忘,跨過世紀的門檻
我們再一次凝視野獸的眼睛。
有黑雪自歷史幽暗的天際飄落
吞咽著詞的灰燼,幸存者們在寒風中
揮手,告別那無法告別的一切
滿載亡靈的船在鐘聲里揚帆……
輪回的夢魘,行尸走肉的命運
我們的臉正被一面鏡子抹去!
當時光甜美的肉身耗盡,火焰熄滅時
我們的心對著愛的遺骸狂吠不已。
為了能夠相愛,必須重新發明愛情
變形、解體,穿越旗幟的陰影和光之浩
瀚
我們重逢于一間恒星的教室,
遙遠的祖國傳來大地之血的轟鳴。
2023年2月
10.失樂園
那么,我們準備帶著蛇出發吧
他已經做出了決定。
面無表情的迦百列垂手而立
天使們揮舞著火焰利劍,
看守著生命之樹。
這并非你的過錯
那果實只能由你遞給我
在這伊甸的搖籃,
我們已沉睡得太久
剎那間:一切都變得明亮
愛和智慧同時發生
光的暈輪中,你那么耀眼
美得像一道神諭。
他的目光,穿過浩渺的天宇
凝視著我們的赤裸。
盡情引誘我吧,愛人
在你身上,我敲著天堂的門
一場灼熱的雨將我們淋濕
多么甜美的褻瀆!
我們領受你的恩賜:罪和死
更多的愛和智慧將會被生出。
微風輕拂著無花果葉,
是該告別的時候了。
在那顆嶄新的星球上
我們將成為彼此的起源
一同命名、勞作,反抗宇宙之熵
2024年8月

劉蕭的詩里有屬于青年人的憤怒、悲傷與冷峻。而他以同齡人中罕見的強度與銳度,將這些情感和品質轉化為“我們時代的哀歌”——這些詩將個人命運置于歷史斷裂處,凝望“野獸的眼睛”并直面“幻覺的瘟疫”,以飽含痛感的語言捕捉集體記憶中的戰栗與遺忘。在他那里,詩的抒情始終攜帶著思的重量,在“詞的灰燼”與“大地之血的轟鳴”之間,構建出極具張力的語言空間。這個空間既屬于歷史和時間,又屬于存在本身——詩人以詞語為筏,承載著“命運的潮汐”與“必要的惡”,在虛無的國度完成一次次孤絕的航行。當“幸存者們在寒風中揮手,告別那無法告別的一切”,詩人不僅完成了對逝去之物的悼念,更以“甜美的褻瀆”重審著信仰與自由、成長與虛無之間的辯證。因此,劉蕭的詩不僅是個人經驗的書寫,更是對一代人精神處境的映照,以及對詩人之使命的自覺:以“將我們釘入這個世界”的決絕,再次確認生命與寫作的勇氣。
執筆人:一行
首先,非常高興能獲這次拾壹月論壇的新銳詩人獎,這應該是我作為一個詩人第一次在公開場合受到承認,所以對于我而言意義重大。感謝拾壹月詩歌獎的各位評委,同時也要感謝一行老師寫的精彩的頒獎詞,讓我非常的感動,每一句都寫進了我的心坎里。但同時我又多少有些慚愧,因為近兩年我個人的寫作陷入了某種停滯。這一方面可能是因為我關注的重點轉向了理論,另一方面也和我個人的生活處境或者說精神困境有關。
這包含很多方面,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在“后疫情時代”該如何寫詩。疫情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也改變了我對詩歌的看法。我個人的創作主要是在疫情之前,現在回頭去看感覺很可疑。雖然也付出了很多心血,但總體上只是個人語言和心智的操練,是一種歲月靜好的寫作,和時代并沒有什么關聯。在疫情之后我再也不能像之前那樣寫詩了。這里需要我們重新去辨認自己在時代中的位置。某種意義上我們面臨著和杜甫或者是保羅·策蘭相似的處境,在歷經時代的重大轉折之后,該如何處理語言和現實的關系。我在疫情期間寫的幾首詩做了一些嘗試,試圖在自身內部找到一條通往時代整體的道路,但這仍舊是遠遠不夠的。
詩人永遠只能通過語言抵達世界,但語言又常常是無力的。詩人需要克服重重的障礙、穿過重重迷霧才能抵達那個由自我、語言和時代交織構成的詩的入口。對于我而言,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這次獲獎既是一種鼓勵,也是一種鞭策。一行老師的頒獎詞我更多的看作是對于我未來寫作的一種期許,我也希望有一天自己真的能成為那樣的詩人。這是一個新的開始。最后,再一次感謝拾壹月詩社和現場的詩人朋友們!
- END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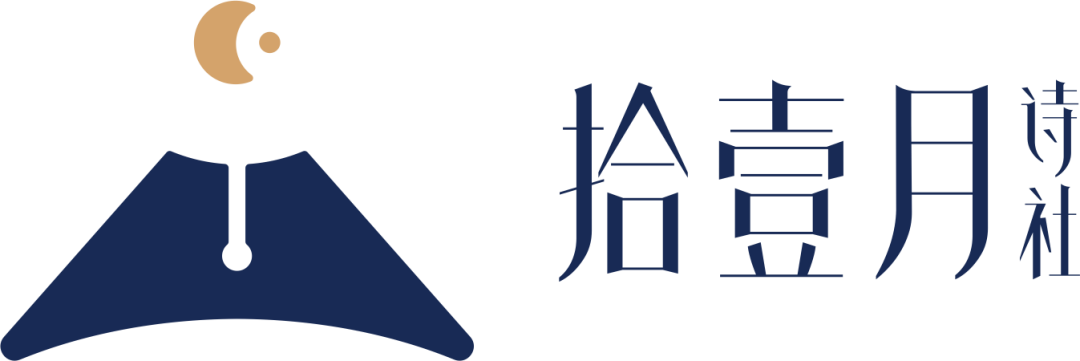
編輯:董君
排版:陳夢凡
審核:拾壹月詩社編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