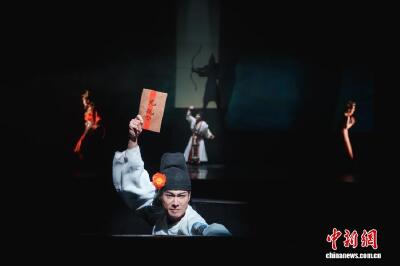宣和殿的窗欞,總映著一方端硯的清輝。硯臺里的徽墨,研了又研,暈開一池澄澈的黑。趙佶握著紫毫筆,指尖輕捻,腕間流轉,瘦勁挺拔的筆畫便落在素箋上,像寒梅枝椏,凌霜傲雪;又像仙鶴翩躚,清逸出塵。那時的他,還不是五國城的階下囚,是大宋的道君皇帝,是書畫史上獨樹一幟的宗師。
他的筆墨里,藏著汴梁的春風。御花園的牡丹開得正好,他便鋪展絹素,以細膩的工筆勾勒花瓣的脈絡,用明艷的朱砂點染花蕊的嬌妍。《芙蓉錦雞圖》里,那只錦雞羽毛斑斕,昂首立于枝頭,芙蓉的柔媚與錦雞的靈動相映成趣,右上方的瘦金體題詩,筆鋒鋒利如刀,卻又透著雅致,詩畫相融,渾然天成。他愛花鳥,愛世間萬物的生機,筆下的《瑞鶴圖》更是驚艷了時光——汴梁宣德門的上空,十八只丹頂鶴盤旋飛舞,姿態各異,天空用石青暈染,澄澈如洗,鶴群的白羽與紅日相映,一派祥瑞氣象。這幅畫里,沒有朝堂的紛爭,沒有百姓的疾苦,只有一個帝王對盛世的期許,對美的極致追求。
瘦金體是他的獨創,是書法史上的一抹孤絕亮色。早年的《楷書千字文》,筆力剛勁,結構疏朗,橫畫收筆帶鉤,豎畫收筆帶點,撇如匕首,捺如切刀,字字風骨峭拔,如玉樹臨風。那時的他,正值盛年,意氣風發,筆下的瘦金體,帶著少年人的鋒芒與俊逸。晚年的《秾芳詩帖》,則添了幾分蒼勁,大字楷書氣勢開張,筆畫瘦硬卻不失腴潤,仿佛歷經歲月沉淀,多了幾分深沉的韻味。他的書法,不像王羲之的飄逸,不像顏真卿的雄渾,獨有一種清瘦挺拔的美,像寒冬里的一枝梅,于冰天雪地里傲然挺立,自有風骨。
他不僅是創作者,更是推動者。他在位時,將畫院納入科舉,以詩題取士,招攬天下畫師。“踏花歸去馬蹄香”,畫師們絞盡腦汁,唯有一人畫出蝴蝶追逐馬蹄的景象,深得他心;“深山藏古寺”,有人畫深山古寺,有人畫山路蜿蜒,而中選者只畫了一個和尚在溪邊挑水,藏露之間,意境悠遠。他以帝王之尊,為書畫藝術開辟了一片沃土,讓宋代的院體畫達到了巔峰。那時的畫院,名家輩出,佳作紛呈,每一幅畫里,都藏著大宋的風雅。
可畫筆終究抵不過金戈鐵馬。宣和七年的秋風,卷著塞外的沙塵,吹破了汴梁的繁華。金兵的鐵騎踏破城門,宮闕傾頹,珍寶被掠,那些他視若珍寶的書畫,有的被付之一炬,有的被擄往北國。他自己,也成了階下囚,從九五之尊淪為“昏德公”,被押解著踏上北行的漫漫長路。
五國城的土屋里,沒有端硯,沒有紫毫,只有粗糙的麻紙和劣質的墨。塞外的風沙磨壞了他的眼睛,卻磨不滅他對書畫的執念。他在昏黃的油燈下,顫抖著提筆,寫下“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斷天南無雁飛”。此時的瘦金體,少了往日的鋒芒,多了幾分蒼涼與悲愴,筆畫里的每一道轉折,都藏著對故國的思念,對命運的無奈。他再也畫不出《瑞鶴圖》的祥瑞,畫不出《芙蓉錦雞圖》的靈動,只能在詩里,在字里,描摹著汴梁的模樣。
他的書畫,是盛世的縮影,也是亂世的悲歌。當故宮的展柜里,《瑞鶴圖》依舊流光溢彩,《楷書千字文》依舊風骨凜然,我們仿佛能看見那個身著道袍的帝王,在宣和殿里揮毫潑墨,眼里滿是對美的熱愛;也能看見那個衣衫襤褸的囚徒,在五國城的寒風里,握著筆,寫下字字泣血的詩篇。
有人說,他是昏君,耽于書畫,荒廢朝政,導致了靖康之恥。可誰又能懂,他本是天生的藝術家,錯生在了帝王家。他的筆墨,本應在江南的煙雨里,在汴梁的春風里,自在生長,卻偏偏被裹挾進了王朝的興衰,染上了血與淚的顏色。
瘦金凝墨,風骨殘山河。他的書畫,是大宋風雅的絕唱,也是一個帝王的悲劇。八百多年過去了,汴河的水依舊東流,五國城的風雪早已消散,可那些藏在筆墨里的風骨與蒼涼,卻永遠留在了歷史的長卷上,讓后人讀之,忍不住一聲長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