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來源于云谷教育,作者品牌傳播中心

“讓每一位孩子成為最好的自己”是云谷學校的使命,我們培養具有仁愛精神、獨立意志、社會擔當、終身學習力和幸福感的地球公民;我們通過科技的力量,讓優質教育惠及更多的孩子,讓東方智慧和世界文明相融合。

來到云谷之前,我讀了一本記錄云谷故事的書《學校進化論》。書中有一些場景,會讓我很自然地進入一種理想主義的想象:

“(2017年)即將離開良渚臨時場地時,核心團隊成員留下來復盤,過程中很多老師都哭了...復盤正進行到一半,突然停電,黑黢黢的房間里一個接一個傳來團隊伙伴的聲音。泠然打開手機電筒,照著白板,一筆一劃的記錄下大家的感受。”(P38)
同樣在這本書里,我還讀到了許多關于云谷的具體做法,比如 1P5C 素養、721 學習法、教育合伙人、學習成長階梯圖、學科熱力貢獻圖等等。但是,看到這些名詞的瞬間,我馬上聯想到一些互聯網行業里常見的一些“黑話”,比如顆粒度、組合拳、垂直領域、底層邏輯。
我不是來批評云谷的,但我確實意識到:教育中一定存在悖論。一方面,我們心中的教育應當是一件充滿理想主義的事情;另一方面,在實際工作中,我們又常常經歷各種掙扎。理想教育似乎應該是開放、自由的;但在現實中,我們又往往需要通過規則、方法和一定的流程來落實它。
我發現云谷的各位同仁也早已意識到這一點。馮晨校長在一篇文章中記錄道:
“現場教師追問,為什么學校的目標指向‘讓老師幸福感綻放’,而達成目標的關鍵行動卻都是‘捆綁’教師的條條框框。”(P47)
顯然,作為教育人,我們都感受到了某些悖論,也非常清楚,僅靠理想主義,撐不起長路。也許,每位教育人都工作在教育的悖論之中,這是我讀完云谷故事后得出的判斷。
所以,今天我想從三個方面來談談我對教育悖論的理解。

目標:教育是否應該有目標?
教育是否應該有目標?我們不妨假設,如果教育沒有目標,會怎么樣?
近年出版的一本書《為什么偉大不能被計劃》,由兩位人工智能領域的專家 Kenneth Stanley 和 Joel Lehman 寫就,他們在書中分享了一些科學家是如何通過“無目標”過程找到突破性解決方案的。
以訓練機器人走出迷宮為例:如果沿用“到達目標”的慣性思維,直線無疑是最短的路線;但按這種方式訓練,機器人將一直在墻上撞。于是有科學家提出,機器人不能靠“直奔目標”的方式完成迷宮任務,而應該學會走“novel stepping stones”(新奇道路)。這些路徑看似與終點無關,卻可能引出意想不到的解法。
類比于人,當一個人認為自己能夠清晰預測未來時,這個未來,未必就是Ta真正會走的方向;而通過“新奇之路”的探索,我們反而更有可能抵達那些原本看似遙不可及之處。
那么,這樣真的對嗎?
教育真的可以“不設目標”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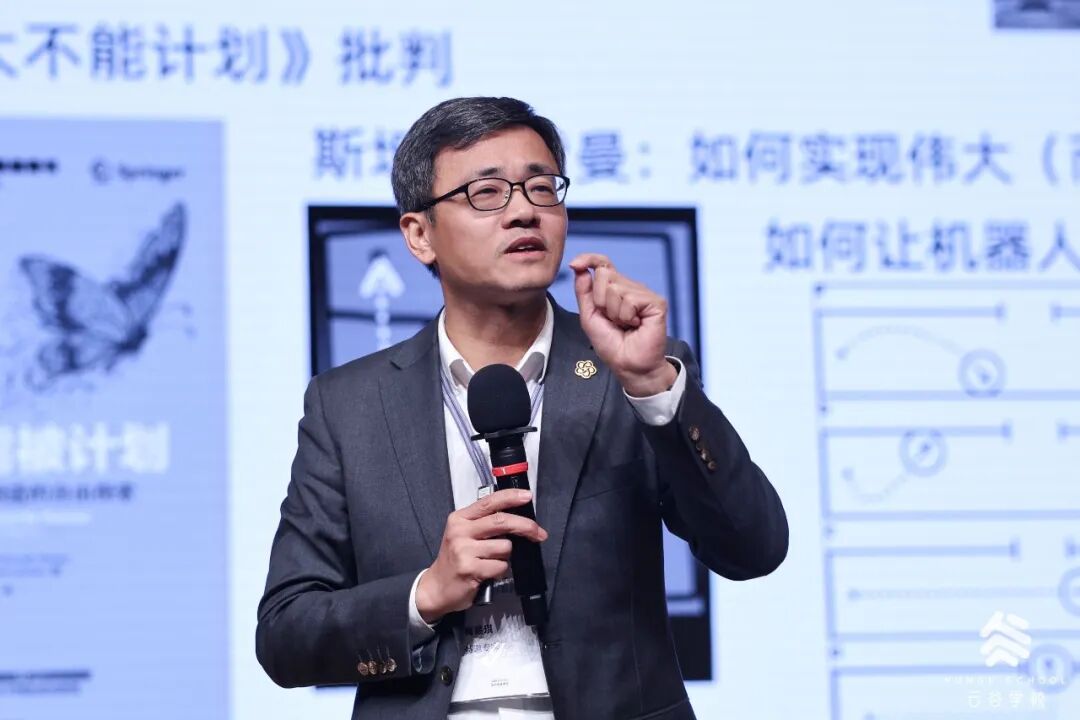
顯然不是。
“無用之用”的最終落腳點依舊是“用”,而不是徹底的“無用”。
如果教育者也完全不設目標,讓“新奇道路”帶著學生隨意去往任何地方,其結果可能是:孩子們最終走向許多我們從未預料、也未必期望的方向——這幾乎是所有教育者都不愿看到的。
沒有目標不行,那我們再回過頭來看:如果教育擁有非常清晰的衡量尺度,又會怎樣?
回到我所在的高校場景。這些年幾乎所有中國高校都非常在乎自己在QS, 泰晤士、USNews和軟科四大排名的的位置。我所在的大學去年也非常高興地發現自己四大排名中都進入了前20名。
但是,我們需要退一步捫心自問:
為什么我們會如此在意這個排名?
當存在一個“清晰標準”為目標時,為什么那些特別優秀的人物,似乎就不得不在探索星辰大海的同時,也把注意力投入到某一個具體排名的爭奪之中?
有人可能會說,明確的標準可以倒逼優化與進步,讓我們可以“從目標到實質”,由外向內地變成想要成為的樣子。
但現實往往并非如此,一旦有測量,就必然會產生扭曲。當教育擁有一個可量化的目標時,無論我們多么努力想要淡化它,只要它存在,就會不可避免地帶來扭曲。這也是我對云谷的一個提醒:不要成為被目標牽著走的組織。
沒有目標不行,有目標又會扭曲。那么除了扭曲之外,目標還有沒有其他價值?
我們來看一個馬斯克的故事。
許多人好奇:馬斯克為什么要去火星?馬斯克的一個回答是:我們之所以確立“去火星”這個目標,并不是因為火星本身,而是因為在努力達成這個目標的過程中,人類會被推動著拓展現有知識的深度與廣度。
去火星的意義并不在火星本身,而在通向火星的路上,我們得以完成許多原本無法想象的事。
聽起來可能有點抽象,我給大家一個真實的例子。
今天的孩子幾乎都是用尿不濕長大的。那尿不濕是怎么來的?它源自人類征服月球的過程。由于阿波羅計劃中,宇航員在飛船里停留時間很長,無法使用傳統廁所,NASA(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提出了一個全新的需求:研制一種能夠快速吸收大量液體,且長期貼身安全的新型材料。這項技術促成了現代尿不濕技術的發展。類似的案例還有很多,我們一起來看看 NASA 最偉大的十項發明。

再給大家分享一個我們新雅書院的故事——關于“兩根搟面杖”。
在新雅,我們有一個系列活動叫「從游」,從游中,又有一個項目叫“一事計劃”。為什么要做一事計劃?其實是受王陽明“事上磨練”的思想啟發,我們希望學生在完成實際項目的過程中學會做事,學會承擔責任。
其中有一個項目叫“南十北家鄉味”(南十北是新雅書院的所在地),它會讓同學們自己來呈現中國某一省份的特色美食。
籌備黑龍江美食節時,就有了“兩根搟面杖”的故事。
黑龍江美食自然離不開面食,而做面食就需要搟面杖。兩根搟面杖,在淘寶上的價格是3塊9毛9包郵,但我們的同學們當時做了一個錯誤而偉大的決定:他們不打算網購。
有位同學靈機一動提出,新雅的儲藏間里肯定有搟面杖,這樣還能節省 3塊9毛9。于是,他們懷著呈現美食的目標,走進了新雅使用八年、從未整理過的儲藏間。為了找到搟面杖,他們花了兩個下午收拾儲藏間。
而且他們好像并沒有找到搟面杖。

(新雅書院儲藏間)
但是他們得到的收獲,遠不止于兩根搟面杖。
有個同學一直帶著堅持戴著口罩在儲藏間整理。每翻出一件物品,他都會說:“你記得嗎?這是我們 XX 年學生節的東西。”“這是某位同學送給另一位同學的禮物。”“這是我們當年為邀請來的那位特別喜歡的學者制作的易拉寶。”
看著他,我突然想到,他其實特別像另一個人——哥倫布。他們的共同點是:
出發前的目標都非常明確,但最后實現的結果卻與原先目標完全背道而馳。但是,就算背道而馳,又有什么關系呢?
哥倫布一生四次抵達新大陸,直到去世,他仍然認為自己到達的是印度,而不是美洲。他到底有沒有真的抵達印度重要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當他開始出發的時候,他已經開始做許多事情了。
所以,教育里到底要不要有目標?我愿意用射擊訓練中的一句話來回答——“有意瞄準,無意擊發”。
帶著這樣的心態看教育,我們會發現:
教育里,最重要的不是“目標本身”,而是我們樹立一個方向,讓學生真正開始出發。
只要出發,只要學起來,只要干起來,你的人生就會是一幅逐漸在眼前展開的畫卷。

組織:教育能被組織化/科技化嗎?
教育能夠被組織化/科技化嗎?我們也從兩個方面來思考它。先看A面:如果教育沒有被組織化會怎么樣?
組織化在今天其實是很被唾棄的一件事,很多時候,人們只要看到教育被組織化了,就會批評它功利化,失去了最應該有的初心。但這種批評本身非常 “cheap”,因為這些批評實際上在做兩件事:
1.設置虛假的標桿;
2.持續生產焦慮。
比如,世界上是否真的存在完全按照“自由方式”來管理教育的例子?其中一個經常被引用的“虛假標桿”是柏林洪堡大學。洪堡大學是 1810 年德國成立的第一所現代大學,被視為世界研究型大學的鼻祖。教育研究者常把洪堡大學當作“自由教育”的最高典范,并且常常提及創辦人洪堡本人的理念——科學的探求、個性與道德的修養、寂寞與自由。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洪堡的理念被廣泛宣揚,但實際上,自理念提出之初,德國學者就已經意識到:洪堡本人理念從來沒有在現實中真正實現過。
教育之所以能夠有效,正是因為它高度組織化;洪堡大學本身就是一所高度組織化的大學。
德國學者門策在上世紀 70 年代就說過:
世界上存在兩種洪堡傳統,一種是“洪堡本人的傳統”,一種是“洪堡大學的傳統”。
另一個“虛假標桿”,基礎教育界的老師可能更熟悉:蘇教版小學四年級語文教材里的《最佳路徑》。故事說,迪士尼樂園建成后,卻還沒有設計連接各景點的道路,于是求助世界著名建筑師格羅佩斯。格羅佩斯沒有直接設計道路,而是撒下草籽,讓游客自由行走,再根據踩出的路徑建人行道。如魯迅所說的,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這個故事給很多人帶來一種浪漫想象:最自然的路徑,才是最好的路徑。但當我第一次看到它時,就很懷疑。于是馬上打電話問在迪士尼工作的同學。同學說:“我從來沒聽說過這個故事,大概率是編的。”
后來我特意研究了格羅佩斯,他是世界上第一座包豪斯建筑的設計者,而包豪斯的核心理念是:形式追隨功能。
一個設計出極簡、方正、結構嚴謹建筑的人,恐怕很難在現實中做出所謂“自由選擇導致最佳路徑”的設計案例。
在教育中,其實我們也常制造類似神話,以證明“非組織化”會帶來自由。但事實上,這往往是一種虛幻的判斷。

包豪斯建筑(圖片來自網絡)
A 面看完了,我們再來看 B 面:如果教育被組織化了,會怎么樣?
組織化的時代沒有英雄,甚至可能長期抑制英雄。今天,幾乎所有大學的專業都有自己的「培養計劃」。但我們不妨追問:大學真的能夠依靠這些培養方案,把學生培養成某一學科的領軍人物嗎?如果你去問每一位院士,你會發現,他們之中許多人在大學時并沒有把培養方案中的每一門課都學得特別好,甚至培養方案里的內容對他們的幫助并沒有那么大。
那么,組織化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培根說過一句話:“真理在錯誤中前進的速度,比在混亂中更快。”之所以要做組織化,并不是因為組織化天然正確;它可能是錯誤的,但至少它不是混亂的,而這正是組織化最核心的價值所在。
但是教育一旦被組織化,人們往往會發現,僵化隨之而來。我們可以借高分子化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張希分享的一個案例來思考僵化的后果。張希老師在最近一期《中國化學會會刊》的主編寄語中講述了色譜法在化學史上的故事,并提出一個問題:為什么作為更優秀分離技術的色譜法會被長期冷落?
色譜法論文發表后的整整二十年間,主流學界始終對這一新興技術敬而遠之。其核心的原因在于:在那個時代,被組織化所認可的“正確方法”是結晶法,而不是色譜法。所以盡管色譜法不需要結晶就可以實現分離技術,但是“一定要結晶”的“祖宗教訓”很容易就阻止了色譜法的流行。
在這篇寄語中,張希老師還引用了莎士比亞的一句話:“期望落空,總在眾望所歸之處;希望常現,總在心灰意冷之時。”如果把這句話借來討論“教育是否應該組織化”,我們會發現:
當組織足夠強大時,反而常是期望最容易落空的時候;而創新的可能性,往往出現在組織的邊緣地帶。
看起來,沒有組織化是虛妄的,有組織化就是僵化的。面對這樣組織化悖論,我的觀點是:
要在充分認識差異的前提下,建立組織中兩類人之間的共識:一類是樹立教育理念和原則的人;另一類是具體實施操作的人。
這兩類人要互相理解。
教育本身是一種農業,但一定是“設施農業”,而不是天然農業。
設施農業意味著一定會有一個大棚,由具體實施操作的人來建設的、有基本的架構的大棚,而從事教育農業的人,也就是那些樹立理念和原則的人,必須要理解這些設施存在的必要性。

反過來,那些具體實施的人,也一定要想辦法多理解樹立理念和原則的人。
云谷有許多從事技術的老師。在討論技術化時,我們也要意識到一個關鍵點:技術為何能夠改變人類生活?人類始終生活在技術與組織不斷互相塑造的關系之中。技術要真正進入生活,必須先理解“人”。
在這一點上,我非常欣賞云谷的一個做法:工程師會走進教師的課堂,在真實教學情境中思考如何設計操作系統和數據庫。

實施:學生究竟是學會的還是教會的?
在教育的實踐過程中,我們還常會遇到一個悖論:學生究竟是“學會的”,還是被“教會的”?
我第一次意識到這個問題,其實是我自己在清華做學生的時候。老師在講臺上講得非常投入,然后問:“同學們,是不是這樣?”前排的學生們都會點頭,而后排的我則心想:你們點什么頭?我還沒聽懂呢。
現在我當了老師,我越來越明白前排點頭的人其實未必真的聽懂,他們只是“習慣性地點頭”。這種現象在今天的大學課堂里非常常見,也因為此,我一直對“我們是否能真的教會學生”這件事情心存懷疑。
這個懷疑直到后來才被徹底證實。
前幾年,清華美院的一位泰斗級教授開了一門非常棒的公益美術課。我從小“手殘”,完全不會畫畫,遇到這門線上課,感慨終于有機會向大師學習了,于是非常認真地看完了整門課程。
老師說,這個世界看似復雜,但在畫畫人的眼里,只需要兩個形狀就夠了——圓和方。然后,他畫了許多的圓和方,這部分我完全理解。但接下來,他開始畫“福娃”了,我就抓瞎了。這時意識到,我并不是想從他那里學“圓和方”;我想學的是他是怎樣做到從我會的“圓和方”畫出我不會的福娃的。
相信很多人也有類似的體驗,比如,你可能收藏過某個視頻“教你如何正確疊衣服”,視頻里只要三下兩下就能疊出一件整整齊齊的衣服,看著特別解壓;但輪到自己時卻完全無從下手,反復抓瞎。
為什么會這樣?
因為緘默知識的大量存在。
現在很多老師為了讓課程變得生動,會講故事、講段子、講人生哲理,有不少老師因為講人生哲理而走紅,大家紛紛點贊,認為這才是“優秀的老師”。但可怕的是,學生聽懂了人生哲理,卻依然不懂課程內容。
學生之所以難以“被教會”,核心原因不是老師不夠生動,而是緘默知識大量存在,以一種“日用而不知”,且高度個性化的方式存在。
世界上只有一種微積分,但每個人學會微積分的方式卻都是獨一無二的。
當教育者試圖把大量的緘默知識顯性化時,恰恰忽略了一個事實:這也在“殺死”其他的學習可能性。
我反而認為,在教育過程中,“學生不能被教會”恰恰是一件好事,這能夠留出空間讓“學生自己學會”。
接下來,我們要繼續追問:學生真的能夠“自己學會”嗎?
很多人聽過蘇格拉底那句著名的話:“教育不是把桶裝滿,而是把火點燃。” 蘇格拉底在《美諾篇》中講過一個經典故事,常被用來證明“啟發式教學”的力量。他認為,學習不是教出來的,只要啟發得好,學生一定會自己學會。
于是他舉了一個例子:如何讓一個奴隸小孩學會畢達哥拉斯定理(勾股定理)。
他的邏輯大致如下:讓孩子想象一個 2×2 的正方形,問它的面積擴大兩倍后,新的邊長是多少。蘇格拉底通過不斷提問與否定,引導孩子觀察圖形,把2*2正方形切成兩個一樣的三角形,然后用四片三角形重新拼成一個新的正方形,由此“推導”出新的面積是原來的兩倍,并且證明了畢達哥拉斯定理。
這個故事聽起來很神奇,但事實上,正如我們今天在現場一樣,大多數人并不能通過類似蘇格拉底追問的方式學會勾股定理,因為缺少許多基本知識前提,例如正方形的面積如何計算。

看起來,教是教不會的,學也是學不會的。那么怎么辦?
今天很多人說,項目式學習(PBL)可以解決學生“教不會和學不會”的問題。但我認為,我們仍需警惕 PBL 容易讓學生陷入的兩個問題。
1.揮刀亂砍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劉云杉老師曾借由“童子操刀”的概念對項目式學習進行反思。她說這種學習方式可能“用方法消解知識,用個體認知替代集體理性,用高階思維替代真理,將導致’無學而有術’的野蠻的心靈”。我把稱之為PBL“揮刀亂砍”的問題。
2.拔刀四顧心茫然
PBL的另一類問題,我把它稱為“拔刀四顧心茫然”。學生面對 PBL項目,不知從何下手,多數項目也只是低水平重復,原因是很多學生缺乏足夠知識基礎。有的甚至只是套用已經做好的成熟模型,這也導致PBL項目中“拼爹拼媽”容易成功。
事實上,PBL 的價值不在于讓學生解決世界難題,而在于讓他們在過程中獲得“學習的機會”。
我們需要的不是讓學生過早進入真實世界。真實世界其實大部分是簡單的。讓學生過早進入真實世界,有可能會讓他們誤以為“世界如此簡單”。
對于情境式學習來說,學習情境不是越真實越好,而是要讓學習者有合法的邊緣性參與(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的機會。
舉個例子,其實真實開飛機大部分時間是自動駕駛,并不難。學習者只有在模擬艙里“可以犯錯的、大量非典型問題存在的”的情境下才能真正地學會飛行。
以上,就是我對教育中三個悖論的思考。
我特別想說一句,其實沒有人能給教育一個唯一答案。如果有的話,大概率是有意或者無意的欺騙。

*圖片來源于網絡
這兩張照片,不知道大家是否還有印象?2023年6月15日,澳大利亞國家隊和阿根廷隊在北京工體進行了比賽。當天在現場,一個男孩穿著阿根廷隊服,從看臺跳下,沖向梅西,想要擁抱他。
梅西簡單地抱了他一下,但真正讓所有中國球迷記住的,是大馬丁。他在中圈與那個男孩擊掌的瞬間,成為所有人的共同記憶。
當然,這個男孩最后還是被帶離了場地。但如果你看照片,會注意到:他被拖走時,臉上掛著笑容,甚至,連保安臉上也滿是笑意。
后來,在我們新雅書院2023 屆畢業典禮上,我把這段故事加進了畢業發言。我也想用它作為今天分享的結語。
“有個秘密是該告訴你們了。
作為教育者,一方面,我們每個人的心里都住著一個站在球場中圈附近的大馬丁,在少年偶然地挑戰規范和權威的時候,默默地等待跟他擊掌。
另一方面,我們每個人又穿著一身齊整的制服,警惕地盯著應該由我們把守的底線,隨時準備把少年摁倒在地。
這個很矛盾的游戲,我們跟你們就玩到這里了。”
把這句話跟畢業生說出來,是對于教育者的解脫。但遺憾的是,說完之后,我們教育者就要重新回到教育悖論的現實之中。我想,這正是教育者既要保持理想主義,又一定不得不擁抱現實主義的根本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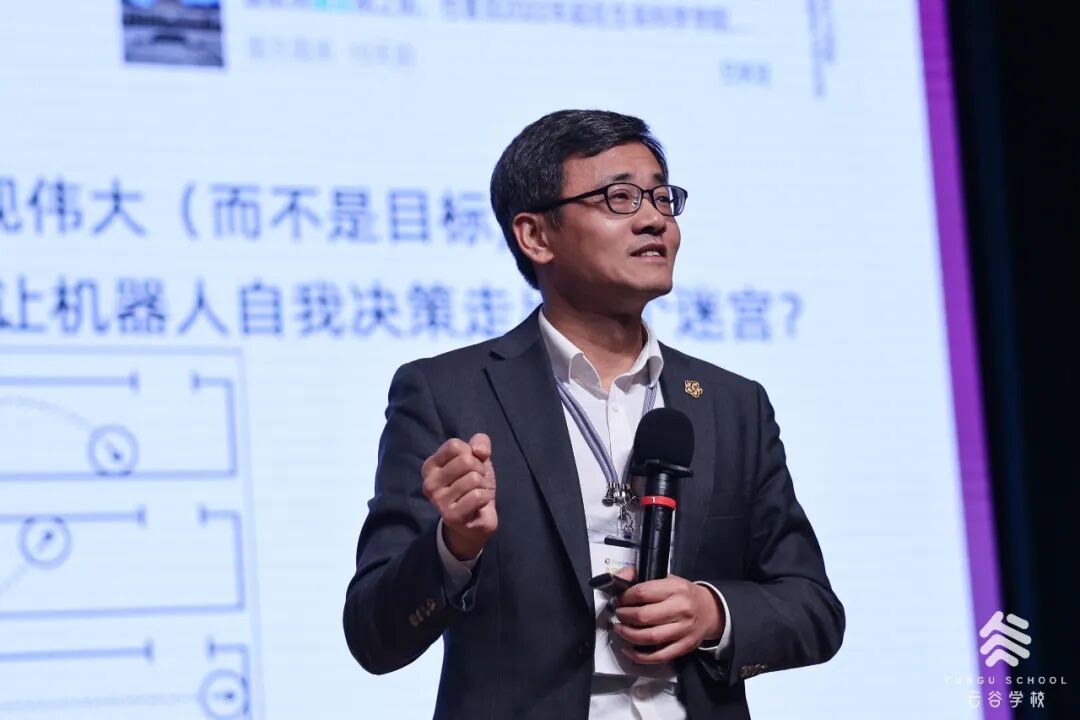
以上,愿與云谷以及所有基礎教育界的同仁們共勉。謝謝各位!

作者丨梅賜琪
來源丨內容來源于梅賜琪教授在云谷學術周開幕式現場分享,轉載自“云谷教育”公眾號
排版丨周壹
聲明丨圖文貴在分享,版權歸原作者及原出處所有。如涉及版權等問題,請及時與我們聯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