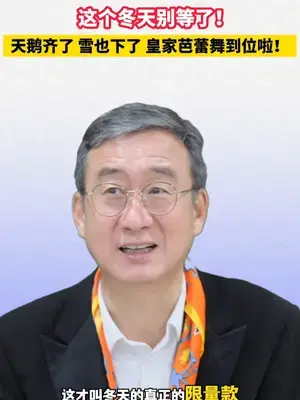這是真正的天鵝芭蕾。
藍(lán)天就是劇場(chǎng),湖邊就是牠的舞臺(tái),牠靜立湖畔,身姿挺拔如一尊白玉雕塑,遙望水天相接之處。忽然雙翼輕展——右翼徐徐打開(kāi),每一根飛羽都在風(fēng)中依次舒展,如同舞者緩緩伸出修長(zhǎng)的手臂。
牠先以肩胛為軸,將右翼向身側(cè)悄然牽動(dòng)——那動(dòng)作如此從容,仿佛不是骨骼與肌肉的伸展,而是一襲白緞被晨風(fēng)徐徐吹開(kāi)。翼尖最先探出,劃破凝滯的空氣,接著是整個(gè)翼面的次第蘇醒:從緊貼肋側(cè)的覆羽開(kāi)始,每一片羽毛都像聽(tīng)從著無(wú)聲的指揮,由內(nèi)而外、由近及遠(yuǎn)地緩緩鋪展。
你能看見(jiàn)那些修長(zhǎng)的初級(jí)飛羽逐一分離,如同折扇上最精致的骨節(jié)優(yōu)雅地張開(kāi);隨后是次級(jí)飛羽,它們層疊展開(kāi)時(shí)泛著絲綢般細(xì)膩的光澤。在舒展至最開(kāi)的一瞬,翼膜輕輕繃緊,露出羽毛基部柔和的灰暈,整只翅膀的弧線完美如古希臘的弓,積蓄著靜默的力量。
整個(gè)過(guò)程中,風(fēng)有了形狀——它從羽梢流過(guò),又被羽軸細(xì)細(xì)梳理;幾顆附在羽緣的水珠倏然滾落,在空中拉出轉(zhuǎn)瞬即逝的銀線。這右翼的舒展并非機(jī)械的打開(kāi),而更像一種沉吟的綻放:每一寸展開(kāi)都在調(diào)整角度,每一根羽毛都在尋找與光、與風(fēng)、與自身重力最和諧的平衡。當(dāng)它完全展開(kāi)時(shí),那翅膀已不僅是肢體,而成了被晨曦重新定義的一片云翳,在湖天之間寫下一道純白而流動(dòng)的頓號(hào)。
接著牠慢慢收攏羽翼,尾羽輕搖,身姿微轉(zhuǎn),隨即仰起優(yōu)雅的頸項(xiàng),抖落一身晨光——那弧線仿佛由最輕柔的樂(lè)句勾勒而成,從平靜的水面緩緩升起,在最高處凝成一個(gè)潔白的問(wèn)號(hào)。隨即,一個(gè)輕盈而有力的頓挫從頸根漾開(kāi),順著流暢的曲線向上傳遞,直至喙尖微微一顫,仿佛撥動(dòng)了空氣中的某根琴弦。
緊接著,那場(chǎng)細(xì)膩的顫動(dòng)傳遍了全身。牠倏然抖羽——并非凌亂地?fù)u散,而是自內(nèi)而外、自上而下地次第綻放:頸間最細(xì)密的絨羽先漾開(kāi)一圈銀閃閃的光暈,隨后背羽如風(fēng)中書(shū)頁(yè)般簌簌翻動(dòng),最后雙翼輕振,無(wú)數(shù)飛羽在同一瞬間釋放積蓄的張力,甩開(kāi)一圈幾乎看不見(jiàn)的、帶著湖水清香的水汽微光。每一根羽毛都在抖動(dòng)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晨曦中鍍上流動(dòng)的釉色。
這仰與抖的銜接,有著天鵝獨(dú)有的韻律:仰是綿長(zhǎng)的詠嘆,抖是靈動(dòng)的顫音;一個(gè)將寧?kù)o積蓄到極致,一個(gè)將生命力迸發(fā)得淋漓——恰似芭蕾舞者完成了一個(gè)極致的arabesque(阿拉貝斯克舞姿)后,腳尖忽然濺起的那些看不見(jiàn)卻感得到的、星光般的震顫。
每一個(gè)動(dòng)作都從容不迫,卻又連貫如一首完整的樂(lè)曲。
湖面倒映著牠潔凈的影子,恍若一場(chǎng)專為天地獻(xiàn)演的水上芭蕾,在這無(wú)人劇場(chǎng)里,完成了最自然的轉(zhuǎn)場(chǎng)。
#拍一拍鄭州疣鼻天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