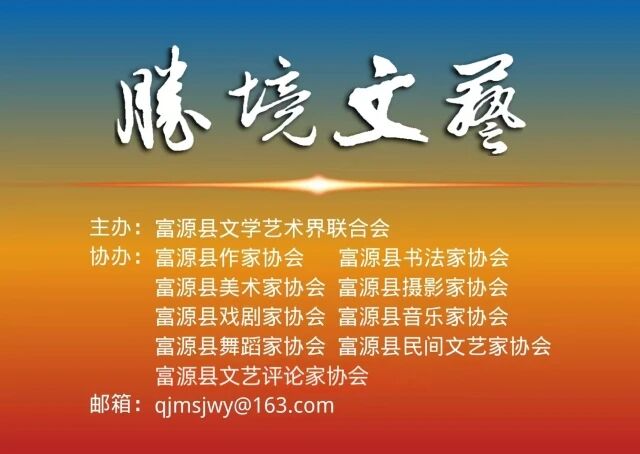我在夕陽下
我在夕陽下,
像一條年邁的河流。
青野碧綠,蝶蜂飛舞,
一道折光,輻射在太行山的縫隙。
蒼天恩典,又過了一年,
那是因為我愛。
愛人,愛己,愛紅塵,
愛著那些有些年輪的樹木,
愛著善惡冷暖,陰晴黑白,
——我從萬物身上汲取光華。
我昂首了一生,
而今匍匐下來,
不看高處:不看太陽、月亮、星星,
它們的燦爛,離我愈遠,
我親吻草根敗葉,覆土塵埃,
——那曾經被我忽略的另一個世間。
我與地面貼緊,很低很低,
那時我看到了自己完整的一生。
夕陽如晦,然千年不墮,
天地間,我在此世,
在往世,
亦在來世。
預言
天地茫茫,霧靄遮覆,
一年一年,就在不經意間冷暖循環。
三月,看華北平原,
浩蕩大河,依然三尺冰封。
天地間的事,許多我們無可奈何,
一個季節和另一個季節,
暑熱寒涼,葉綠葉黃,
時光匆忙,它只告訴我們冷暖,
剩下的,靠我們自己感受。
江河流年,歲月千載,
多的是浮土,少的是青銅,
大鼎大罍,竟在一夜間消失,
剩下的,無非是些落葉殘枝。
浮云濃淡,淺草衰榮,
我們來到世上,
為了說一些話,見一些人,受一些難,
然后,在前人走過的路上重復一次。
原來覺得前人們悲愴,
后來才知道,我比他們更悲愴。
滄海閱盡,無善無惡,
在長江邊望著浩蕩逝水,
總會想起那千古絕唱,
離愁幾載,即是無盡天涯。
所以我預言,百年后的今天,
不會比現在更為滄桑!
一個人走在平原上
一場大雪后,一個人走在平原上,
白茫茫大地遼闊,
河流結冰了,一凍到底。
坎坷的是路,
平坦的下面是河流。
這是一個人的經歷,
也是北方的一段經歷。
大雪中的人們茫然四顧,
因此這一年的北方,
實在沒有什么值得回味和記憶。
那時,一個人在大雪里孤單而深遠,
這個冬天只有覆蓋與傳說。
北方,好大的雪啊。
雪盲,什么也看不清楚,
干什么要看那么清楚,
三分之一的時間看清世相,
三分之一的時間適度模糊,
其余的時間,閉著眼睛。
這一年,僅僅是光陰荏苒的世態里,
一顆微不足道的種子。
記住,我說它是種子,
也許有一天,
這一年就會結果!
我收到過牛漢的一封來信
這張紙一直是白的,
它有呼吸,有血液,
撫摸它,它有熱度,有質感。
陰天沒能把它染黑,
暗夜沒能把它染黑,
世態污濁沒有把它染黑,
天地混沌沒有把它染黑。
這張紙上寫下過很多字,
不一定每個字都有意義,
但每個字都周周正正。
幾十年有少許微黃,也有了褶痕,
但沒有變軟沒有變脆,
鋪在桌上,還是早年的厚度和硬度。
墨跡濃淡,筆力深淺,
天下滄桑,日月久長。
(原載《星星》詩刊2025年第10期)
寫詩就是寫自己——如何寫好一首詩
郁蔥
說到“如何寫好一首詩”這個話題,就想到曾經說過的一句話:“寫詩就是寫自己,寫自己對人、對世界的感知。”詩友問我,這么說是不是有點小?我說不要只看前半句,更重要的是后半句。如果我們這輩子能把自己對人、對世界的認知寫透,就已經很是造化了。我不大注重一位詩人的寫作形式,而是在他的表達中感受文字的獨特性和對我的啟示性。詩歌是詩人對世界的認定方式,詩歌是詩人對自己內心的認定方式,應該讓人能夠在他的詩中感受到所需要的美感和痛感。
我小時候生活在一個不大的縣城,那里不疲憊,不緊湊,如果不去感悟,好像也不會有多少深意,但會培養人恬淡、安然的性格,然后寫一種冷靜、內涵的文字,我一直期待著我能做到這一點。寫作本質上也是生活,有的人越寫心態、狀態越好,越寫越懂得生活。也有的把自己寫得很躁、很鬧,寫得心緒不寧,焦慮難安,這不好。詩歌和寫詩當然是一種極致的美好,但詩壇這個“圈子”也是一個小社會,社會上有的這個圈子里都有。所以我還是重復對年輕詩人們說過的話:第一不趨同,第二不老化,第三不是非。無限地做好自己的事情,做到最好,許多蕪雜就能擺脫。做藝術跟做人基本相通,看人的質量。
詩歌有數不清的定義和概念,有時候連我也搞不清楚。曾經在一次詩會上談到作品的個性,我說:“這是個大話題,但有一句稍感矯情的話可以記住:‘觸碰不可言說的那些文字。’”還記得有句話說:“有些詩是嚷出來的,有些詩是仿出來的,有些詩是想出來的,有些詩是長出來的。”長出來的詩會留住,并且可能會成為經典,而且長出來的詩有一個特征,一定是樸素、好讀的。由于樸素,注定蓬勃。寫詩是由于宣泄的欲念,是由于情感的新發現,寫詩是為了在文字中尋找快樂。我一直在寫,是由于我一直沒有失去這種快樂。當然這些都是情緒,所以對于一個成熟的詩人,不在于如何運用技巧,而在于如何運用情緒。
寫詩最重要的是天分,比天分重要的是經歷。有共同經歷的人就有默契,就能讀懂對方。到了什么年齡,就會有什么年齡的積淀和表達,就應該寫出那個年齡段的相對的經典。我總說詩是等來的,等經歷。天分支撐詩感,經歷造就深度。積淀是一種藝術修養,不隨暑熱秋涼而變化,不因物事欲念而愁苦,往大里說這是境界,往小里說這是性格。而且好詩一定有適度的理性,理性的作品具有恒久性。我能夠記住的多是那些有質感、有韻味、理性的作品,詩中有觸動我的動情點和隱秘點,有我說的“真實的心跳”。說到這里,想起里爾克說過的一句話:“一個人早年的詩是這般缺乏意義,我們應該畢生期待和采集。如果可能,還要悠長的一生;然后,到晚年,或者可以寫出十行好詩。因為詩并不像大眾所想像,徒是情感,而是經驗。”你看,在這一點兒上,我和大師有默契。
還想到寫作的陌生感——對把握的內容和形式的陌生感,這是對自己的挑戰。我寫詩一直在變化,一生求變,這樣不容易形成所謂寫作風格(時髦的詞叫“辨識度”),寫起來不會覺得情緒上勉強,不會有審美疲勞。當然一個人的寫作會有一種內在的氣韻貫穿始終,不管形式、內容、語言有什么變化,這個內核是難以改變的。因此一直主張尊重每位詩人的獨特個性,輕易不用簡單的理解對一位詩人和他的作品做出判斷。我知道詩只可感受不可詮釋,詩是內心的東西,而真正進入一個人的內心,幾無可能。這不是說詩沒有普遍的審美標準,而是在強調藝術的個人特質和多元情感世界中的唯一性。
生活是第一位的,最重要的是生活本身,然后才是寫作。我把平時生活的狀態和寫作時的狀態分得很開。一個詩人智商情商一定相對較高,可一些詩人總是把詩和自己具體的生活攪在一起,說詩是自己的生活方式,這就真的會出問題,更多時候做一個俗人或許才能寫出好詩。當然我還是說所有的道理都有漏洞,一個看似相對完整的理論體系,換一個角度,肯定就有了缺憾,看你強調什么。我曾經談“經典敘事”,現在又談具體生活,各自都有道理,因為任何一種理論都可能很完美同時也很偏頗。
我的寫作習慣跟別人不同,內心緊湊、憂郁成分重的時候,我會寫一些感性、明澄的詩,內心在一段時間變得相對松弛、開闊的時候,反而會寫一些更理性、更內在的詩,幾十年都是這樣。心情壓抑的時候,我寫的詩一定很明朗,而內心放任的時候,我寫的詩一定相對理性和深邃。這種狀態可能與社會現實脫節,我覺得詩人就要適度的與現實保持一段恰當的距離。這也許顯得狹隘,但我很固執。一位論者評價我:“不是一個霸氣、有野心的人,但常有尋常人所沒有的率真、純凈。有一顆底層的悲憫心,創作隨意和感性;有不愿放棄的北方烙印;有樸實的感情和心理底蘊,在這個物質和現實的社會里保持不投降的姿態。”我也很滿足于這種狀態:真純、現實、理想、內涵。
有人說我們這個時代缺乏偉大的詩人,還有人說我們正處于一個詩歌的黃金時代,這兩句話都有道理,一方面,我在《端午記》中曾經寫道:“哪個時代也沒有缺少過寫詩的人,但是缺少用身軀撞門的人,缺少清醒理性、欲求寡淡、一直用血寫詩的人,我不是,我這一代人,都不是!”“用血寫詩”是一位杰出詩人的標志,當代不是“缺乏”,而是基本沒有。第二句話,實際上幾乎所有的時代都不能不說是詩歌的黃金時代,看你怎么把握,看命運了。我又一次提到了這個詞:命運。沒有什么時代的藝術可以復制,除非你所在的那個時代的詩人很沒有尊嚴。
寫詩這東西,別總想“哪條路才是自己應該走的”,沒有一條路絕對準確,許多條路都對。由著心性。朋友對我說他“多寫的是個人的感受”,誰都是這樣,這沒有什么錯。不拒絕宏大也不拒絕私密。不拒絕公眾情感,更不拒絕個人情感。想起來早年有人問彌爾頓,詩應該是什么樣子,彌爾頓回答:“簡單的、感覺的、熱烈的。”這就夠了。還有一句話:“最遠的邊緣,位于藝術與非藝術的交界線上。”史密斯這樣表述的時候,一定是充滿了對藝術和生活的雙重感嘆。時間越輕飄,藝術越沉重。
前幾天在圖書城,看著一些書擺在書架上、堆在墻角里,沒有人翻閱,那么光鮮的印刷品,這么快就成為過去。讓人感慨:有些文字,真不經磨啊!
2025年7月11日
(原載《星星詩刊?詩歌理論》2025年第9期)
【作者簡介】
郁蔥,原名李立叢。當代詩人、散文作家,編審。著有詩集《生存者的背影》《世界的每一個早晨》《郁蔥的詩》等十余部,散文、隨筆集《江河記》《俗生記》《無窮愛》《此生彼生》《藝術筆記》,評論集《談詩錄》《好詩記》等多部。詩集《郁蔥抒情詩》獲第三屆魯迅文學獎,《塵世記》獲塞爾維亞國際詩歌金鑰匙獎。現居石家莊市。
來源:詩賞讀
編輯:詹宇涵
審核:盧志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