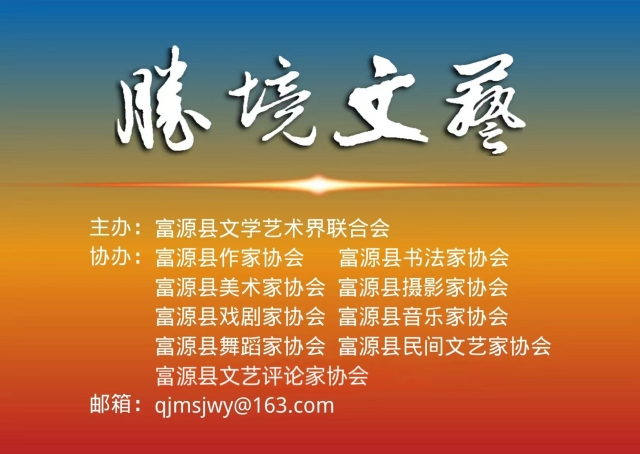01
南下跋涉的頭一天上午,我們的駝隊和畜群長時間穿行在沒完沒了的丘陵地帶。直到正午時分,我們轉過一處高地,視野豁然開闊,眼下一馬平川。大地是淺色的,無邊無際。而天空是深色的,像金屬一樣沉重、光潔、堅硬。天地之間空無一物……像是世界對面的另一個世界,像是世界盡頭的幕布上的世界,像是無法進入的世界。我們還是沉默著慢慢進入了。
走在這樣的大地中央,才感覺到地球真的是圓的——我們甚至可以看到大地真的在往四面八方微微下沉,我們的駝隊正緩緩移動在這球面的最高點
大約兩個小時后,空曠的視野里出現了一長溜鐵絲網。從東到西,攔住了一切。而我們繼續前進。很久以后走到近前,才看到土路與鐵絲網的交叉處有個豁口。穿過這豁口,我們繼續深入大地的西南方向。走了很久很久以后,才看到這鐵絲網的另外一面——仍然橫亙東西,前不見頭后不見尾。
在這荒涼的戈壁灘上,為什么要建造這么巨大的一個工程,圈起如此廣闊無物的土地?
對此,居麻的說法是:為了能讓戈壁灘變得跟喀納斯(阿勒泰最著名的五A級景區)一樣。不準我們的羊再吃草了,只讓野馬去吃,讓黃羊(鵝喉羚)去吃,讓草使勁地長。不然的話,內地人來了,就會說:“都說新疆是好地方,其實啥也沒有嘛,全是戈壁灘嘛!”——草也沒有,野馬也沒有,也拍不成電視,也照不成相。太難看了!太丟臉了!所以一定要保護起來……
我估計這是基層干部們在給動遷的牧民做思想工作時給出的一個不耐煩的解釋。
真正的原因大約是近幾年推行“退牧還草”政策。防止過度放牧,所以進行圈劃,分區輪牧。
據說鐵絲網要圍五年,現在已經圍了三年了。
02
我們的鄰居一家四口,一對夫妻,一個小伙子,一個小嬰兒。男主人就是新什別克。
剛到沙窩子時,我問居麻那家的女主人叫什么,居麻說不知道。又問那個小伙子叫什么,也說不知道。再問他們分別多大年紀,還是不知道。我大為奇怪:“你們不是鄰居嗎?”
后來才知,今年是兩家人開始做鄰居的第一年,其實大家都不太熟的。
往年,眼下這塊數萬畝的牧場上只住著居麻一家人。而新什別克家的牧場正好在鐵絲網圈住的范圍里。被勒令休牧后,雖失去了牧場,卻得到了補償金。于是他們用這補償金重新租借牧場,繼續放羊。這個冬天,新什別克共付給居麻家四千塊錢的租金。因去年雪大,今年春天大地濕潤,牧草額外豐足。因此對居麻家來說,四千塊錢還是很劃算的。
我又打聽了一番,隔壁有兩百多只羊,三十來只大畜(駱駝居多)。一整個冬天下來,每位才攤十幾塊錢的伙食費。真是節約標兵。
03
我們生活剛穩定下來不久,一個大霧的月夜里,兩個迷路的不速之客帶來了一個壞消息,正與這次租借牧場有關。
話說這倆人原本去北面的鄰牧場,結果迷路了,闖入了我們的沙窩子。他們聲稱自己開汽車過來的,顯然那輛汽車肯定不咋樣,因為兩人穿衣的架勢跟騎馬差不多。一位居然套著闊大笨重的生皮的羊皮褲。年輕點的那位像婦人一樣裹著厚墩墩的寶石藍色金絲絨掛面的羊毛馬夾。兩人急于趕路,傳遞完消息,又問清道路,茶也不喝就走了。客人走后,居麻激動又氣憤,就此事逮著嫂子大聲爭論起來,還把嫂子當成對立方呵斥了半天。嫂子始終默默無語地提著紡錘捻羊毛線。
原來這塊牧場并不是居麻一家的,原先屬于三家人共有,大家是鄰居,都住在這個沙窩子里。但其中一家多年前遷去了哈薩克斯坦,另一家也很快改行做起了生意。于是這些年來只有居麻一家守著這幾萬畝荒野,從沒人過問什么。可草場剛租出去,做生意的那家就開始過問了。他家認為新什別克付的租金應該兩家平分,便去鄉領導那里告了狀。居麻大怒,沖我嚷嚷:“他自己又不來放羊了,怪我干啥?別說告到鄉里,就是告到中央也是我有理!”可我覺得他實在沒啥理。
這件事大家議論了兩天,并商量好了說辭,坐等告狀的那家前來理論。可人家才不傻,犯得著嗎?罵個架跑這么遠。調解委員會的自然更不會來了,公家那么窮,哪有錢報銷汽油費。
這事似乎再無后話,大家松了口氣。可我卻始終不安,隱隱感覺到了牧場和牧人日漸微薄的命運。
傳說中最好的牧場是這樣的:那里“奶水像河一樣流淌,云雀在綿羊身上筑巢孵卵”——充分的和平與豐饒。而現實中更多的卻是荒涼和貧瘠,寂寞和無助。現實中,大家還是得年復一年地服從自然的意志,南北折返不已。春天,牧人們追逐著逐步融化的雪線北上,秋天又被大雪驅逐著漸次南下。不停地出發,不停地告別。春天接羔,夏天催膘,秋天配種,冬天孕育。羊的一生是牧人的一年,牧人的一生呢?這綿延千里的家園,這些大地最隱秘微小的褶皺,這每一處最狹小脆弱的棲身之地……青春啊,財富啊,愛情啊,希望啊,全都默默無聲。
前來收購馬匹的一位生意人告訴我:再過兩年——頂多只有兩年時間,就再也看不到這樣搬家游牧的情景了!據說從明年開始,南下的羊群到了烏倫古河畔就停下,再也不會繼續往南深入。
我大吃一驚:“不會吧?這也太快了吧?”
我的反應很令他生氣。他放下茶碗,莊重地面朝我說:“你覺得我們哈薩克受的罪還不夠嗎?”
我噤聲。其實我的意思是,雖說這種古老的傳統生產方式本身正在萎縮,但如此突然的大動作,對人們的生活和心理該是多大的沖擊和搖撼啊。
過了半天我忍不住又問:“是真的嗎?是誰說的?有正式的文件嗎?”
他說:“文件肯定有,我們肯定看不到。反正大家都這么說嘛。”
居麻大喊了一個國家領導人的名字,又嚷嚷道:“是他說的!昨天給我打的電話!”
大家哄堂大笑,轉移了話題。
其實我還想問:“你們覺得定居好嗎?”再一想,真是個蠢問題。定居當然好了!誰不向往體面穩定、舒適安逸的生活呢?
荒野終將被放棄。牧人不再是這片大地的主人。牛羊不再走遍這片大地的每一個角落。本來就貧瘠單薄的植被,將失去它們最重要的養料——牲畜的糞便。而沒有了成群牲畜的反復踩踏,秋天的草籽也失去了使之深扎土壤的力量。它們輕飄飄地浮在干涸的沙地上,扎不下根去,漸漸爛朽,然后在春天的大風中被吹散。脆弱的生態系統越發脆弱。荒野徹底停留在廣闊無助的岑寂之中……荒野終將被放棄。
而在北方,在烏倫古河兩岸,為滿足牧人定居后的需求,大量的荒地將被開墾成農田,饑渴地吮吸唯一的河流。于是河流漸漸斷流,下游的湖泊萎縮,從淡水湖轉變為鹽水湖。魚類面臨滅頂之災。為了讓停止南遷后的畜群度過漫長寒冬,人們無法遵循貧瘠土地只能種兩年停一年的輪耕法則,只能在有限的土地上大量投入化肥,催生肥大多汁的草料。另外,還有定居導致的地下水的抽取,還有生活垃圾的污染……這些還有什么可說的呢?
04
居麻一喝醉了就罵我滾。我要是有志氣,應該甩開門就滾。可甩開門能滾到哪里去呢?門外黃沙漫漫,風雪交加。無論朝著哪個方向,走一個禮拜也走不到公路上去。況且還得拖個比我還大的行李。況且還有狼。只好忍氣吞聲
我剛進入這片荒野的時候,大家給我安排的工作不是太多。每天下午干完自己的活,趁天氣好,總會一個人出去走很遠很遠。我曾以我們的黑色沙窩子為中心,朝著四面八方各走過好幾公里。每當我穿過一片曠野,爬上曠野盡頭最高的沙丘,看到的仍是另一片曠野,以及這曠野盡頭的另一道沙梁。無窮無盡。——當我又一次爬上一個高處,多么希望能突然看到遠處的人居和炊煙啊!可什么也沒有,連一個騎馬而來的影子都沒有。天空永遠嚴絲合縫地扣在大地上,深藍,單調,一成不變。黃昏斜陽橫掃,草地異常放光。那時最美的草是一種纖細的白草,一根一根筆直地立在暮色中,通體明亮。它們的黑暗全給了它們的陰影。它們的陰影長長地拖往東方,像魚汛時節的魚群一樣整齊有序地行進在大地上,力量深沉。
走了很久很久,很靜很靜。一回頭,我們的羊群陡然出現在身后幾十米遠處(剛到的頭幾天,無人管理羊群,任它們自己在附近移動),默默埋首大地,啃食枯草。這么地安靜。記得不久之前身后還是一片空茫的。它們是從哪里出現的?它們為何要如此耐心地、小心地靠近我?我這樣一個軟弱單薄的人,有什么可依賴的呢?
05
在這無可憑附的荒野,人又能依賴什么呢?我們安定下來的第二天,就在沙窩子附近的沙丘最高處插了一把鐵锨,掛了一件舊大衣。遠遠看去,像是站了個人在那里——用以嚇唬狼。剛駐扎下來時,有尋找駱駝途經此地的牧人繞道前來提醒:前幾日,兩只狼在大白天里襲擊了羊群,咬死了四只羊。
從此,這個假人成為我們的地標。無論走多遠,只要回頭看到它還好端端地站在那里,心里便踏實。反之則心慌意亂,東南西北一下子全亂套了。尤其是陰天里。
略懂漢語的居麻對“迷路”一詞的翻譯是“忘了”。他說:“今天下午嘛,我又‘忘了’。羊在哪個地方,我在哪個地方,這邊那邊,不知道了嘛!”
我試著打聽過我們待的這個地方叫什么地名,但這么簡單的問題,居麻卻怎么也領會不了。于是直到現在我都沒弄清自己到底在茫茫大地的哪一個角落度過了一整個冬天……只知道那里位于阿克哈拉的西南方向,行程估計不到兩百公里。騎馬用了三天。緊挨著杜熱鄉的牧場。地勢東高西低。據我的初步了解,這一帶能串門的鄰居(騎馬路程在一日之內)有二十來戶。每戶人口很少有超過四個人的。總共十來塊牧場,每塊牧場面積在兩萬至三萬畝之間。大致算下來,每平方公里不到二分之一個人。后來我在牧畜局查了一下有關數據,密度比這個還小。整個富蘊縣的冬季牧場,每平方公里不到四分之一個人。
放下茶碗,起身告辭的人,門一打開,投入寒冷與廣闊之中;門一合上,就傳來了他的歌聲。就連我,每當走出地窩子不到三步遠,也總忍不住放聲唱歌呢!大約因為,進入荒野,當你微弱得只剩呼吸時,感到什么也無法填滿眼前的空曠與闊大時,就只好唱起歌來。只好用歌聲去放大自己的氣息,用歌聲去占據廣闊的安靜。
06
加瑪一直戴著一對廉價又粗糙的紅色假水鉆的耳環。才開始我覺得俗氣極了。很快卻發現,它們的紅色和它們的亮閃閃在這荒野中簡直如同另外的太陽和月亮那樣光華動人!
另外她還有一枚鑲有粉紅色碧璽的銀戒指。這個可是貨真價實的值錢貨,便更顯得她雙手的一舉一動都美好又矜持。
我還見過許多年邁的、辛勞一生的哈薩克婦人,她們枯老而扭曲的雙手上戴滿碩大耀眼的寶石戒指。這些夸張的飾物令她們黯淡的生命充滿尊嚴,閃耀著她們樸素一生里全部的榮耀與傲慢。——這里畢竟是荒野啊,單調、空曠、沉寂、艱辛。再微小的裝飾物出現在這里,都忍不住用意濃烈、大放光彩。
有一天加瑪在一件舊衣服的口袋深處摸到了一枚假金戒指。當時已經擠得皺皺巴巴,擰成了一團。居麻把它掰直了,再套在一根鐵棍上敲敲砸砸一番,使之恢復了原狀。為表示友誼,加瑪把它送給了我。我非常喜歡,因為它看上去和真的金子一模一樣。若是以前,我說什么也不會把這樣的假東西戴在手上的。可如今,在荒野深處這個儉樸甚至寒磣的家庭里,在僅備最基本日常用具的生活里,在空無一物的天地間,它是我唯一的修飾,是我莫大的安慰。它提醒自己是女性,并且是有希望和熱情的……每當我趕著小牛向荒野深處走去,總是忍不住不時用右手去撫摸左手的手指,好像那枚戒指是我身體外部唯一的觸角,唯一的柄持,唯一的開啟之處。在藍天下,它總是那么明亮而意味深長。
07
十二月初,每隔兩三天,就會有南遷的披紅掛彩的駝隊和羊群遙遠地經過我們的牧場。我和加瑪高高站在沙丘上,長時間目送他們遠去。默數他們的駱駝數量,判斷他們的財富。什么也不為,什么也不說。他們的行進真是驕傲又孤獨。在荒野中他們最倔強。
有一天早茶后,加瑪喚我出去。我一看,又一支隊伍經過西面的荒野向南慢慢行進著。但是加瑪又提醒我:“看,沒有馬。”仔細一看,果然,隊伍里只有一個人步行牽著駝隊,同時還兼顧趕羊。看來看去再也沒有別的人了。比起之前幾支又是摩托車又是座飾華美的馬匹的隊伍,這可真寒磣啊。加瑪判斷道:沒有馬是因為他家昨夜駐扎時,馬跑散了;只有一個人前進是因為其他人都找馬去了。
無論如何,那情景讓人看了很是辛酸。這是荒野,什么樣的挫折都得接受,什么樣的災難都得吞咽。
來源:花城出版社
編輯:詹宇涵
審核:盧志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