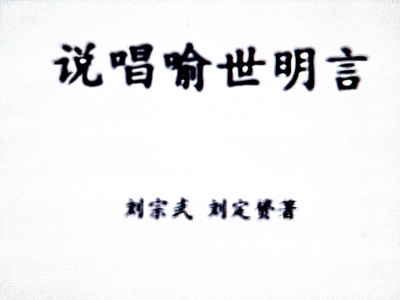第一章:船模與夏夜
青溪鎮的夏夜,總帶著股潮濕的水汽。沈亦舟蹲在河邊的石階上,手里摩挲著個巴掌大的銅船模,月光灑在水面上,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長,晃晃悠悠地浸在水里,像條不安分的魚。
“弄好了?”林晚秋從身后走來,手里端著個粗瓷碗,碗里飄著淡淡的荷葉香。她走到他身邊坐下,把碗遞過去:“娘煮的荷葉粥,放了點冰糖,你嘗嘗。”
沈亦舟接過碗,卻沒喝,只是把船模往她面前湊了湊。那船模做得真精致,船身刻著細密的水波紋,桅桿上還系著根紅繩,被他摩挲得發亮。“你看這船艙,能打開。”他獻寶似的撥了下船底的機關,小小的艙門“咔嗒”一聲彈開,里面竟還放著個更小的銅人,穿著粗布褂子,眉眼依稀是他的模樣。
林晚秋“噗嗤”笑了出來,指尖輕輕碰了碰那小銅人:“你這手藝,不去學打鐵可惜了。”
“等咱們到了鐵城,我就去鐵廠當學徒,天天給你打這些小玩意兒。”沈亦舟仰頭喝了口粥,冰糖的甜混著荷葉的清,在舌尖漫開來。他放下碗,認真地看著她,“后天卯時,渡口見。我已經跟老船夫說好了,他會把船停在柳樹下,咱們一上去,他就開船,直接順流往下走,天亮就能到鐵城碼頭。”
林晚秋的心跳漏了一拍,指尖攥緊了衣角。她望著水面上晃動的月影,輕聲問:“真的……不用跟家里說一聲嗎?”
“說了還走得成?”沈亦舟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微涼,在夏夜里帶著點顫抖,“你娘那脾氣,不把我腿打斷才怪。等咱們在鐵城站穩了腳跟,我再回來提親,到時候生米煮成熟飯,她還能不認我這個女婿?”
他說得篤定,眼里閃著光,像藏著整片星空。林晚秋看著他年輕的臉,月光在他眉骨上投下淺淺的陰影,竟讓她想起小時候聽書人講的那些俠客,一身孤勇,只為心中的念想。
“船模我收著。”她抽回手,小心翼翼地把銅船模放進貼身的布包里,“到了鐵城,你可得說話算數,天天給我打小玩意兒。”
“一言為定。”沈亦舟笑得露出兩顆小虎牙,“到時候我給你打個銅鐲子,上面刻滿花紋,比鎮上銀鋪里的好看十倍。”
兩人坐在石階上,沒再說話。河水“嘩嘩”地流著,帶著夜蟲的鳴唱,把時光泡得軟軟的。遠處傳來幾聲犬吠,又很快沉寂下去,只剩下彼此的呼吸聲,在寂靜的夏夜里,輕輕起伏。
林晚秋低頭摸著布包里硬硬的船模,心里像揣了只小兔子,既緊張又期待。她偷偷抬眼,看了看身邊的沈亦舟,他正望著遠處黑黢黢的河道,嘴角還掛著笑,仿佛已經看到了他們在鐵城的新生活。
她輕輕嘆了口氣,把布包往懷里又塞了塞。不管前路如何,能和他一起走,好像再難的日子,也變得有了盼頭。
夜風拂過,帶著水汽的涼,吹起林晚秋鬢角的碎發。沈亦舟伸手替她把頭發別到耳后,指尖不經意擦過她的臉頰,像羽毛拂過心尖,癢癢的,麻麻的。
“回去吧。”他低聲說,“早點睡,養足精神,后天好趕路。”
林晚秋點點頭,站起身,卻又被他拉住。
“這個給你。”沈亦舟從口袋里掏出個東西,塞進她手里,“防身用的。”
她攤開手,借著月光一看,是把小小的銅制小刀,刀柄上纏著紅繩,和船模上的那根一模一樣。
“別擔心,”他看著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說,“有我在。”
林晚秋握緊了小刀,紅繩硌著掌心,卻帶來一種奇異的安穩。她點點頭,轉身往巷口走去,走了幾步,回頭看時,沈亦舟還站在石階上,對著她的方向揮手。月光落在他身上,像給他鍍了層銀,明明離得不遠,卻莫名生出種“此去經年”的錯覺。
她深吸一口氣,轉身快步走進巷子里,布包里的船模硌著胸口,像個滾燙的秘密。
第二章:未拆的信
天還沒亮透,青石板路上就響起了腳步聲。林晚秋揣著布包,腳步輕快又緊張,露水打濕了褲腳,涼絲絲的,卻壓不住心里的熱。渡口的柳樹下,果然泊著艘小漁船,老船夫蹲在船頭抽煙,見她來,磕了磕煙灰,朝身后努了努嘴:“早等你了。”
沈亦舟正坐在船尾擺弄船槳,見她上來,趕緊起身扶了一把,掌心的溫度燙得她指尖發麻。“快坐,我給你留了靠里的位置,風小。”他笑得一臉燦爛,眼角眉梢都是藏不住的雀躍。
林晚秋剛坐下,就見沈亦舟從懷里掏出個油紙包,打開是兩個熱乎的白面饅頭,還冒著氣:“王嬸今早特意給我蒸的,加了糖,你嘗嘗。”
她咬了一口,甜絲絲的面香混著麥香在嘴里散開,剛想說“好吃”,就聽見岸上傳來急促的腳步聲,還有娘尖利的叫喊:“林晚秋!你給我站住!”
沈亦舟手一緊,船槳“咚”地磕在船幫上。老船夫見狀,猛地撐起篙,小船“吱呀”一聲離了岸,往河心漂去。
“娘!”林晚秋扒著船舷往后看,娘被爹死死拽著,頭發散亂,正朝她揮手,眼淚混著晨露往下掉。她心里一酸,眼圈也紅了,手里的饅頭攥得變形。
“別回頭!”沈亦舟按住她的肩,聲音發沉,“等咱們安定了,我陪你回來賠罪。”他從懷里掏出封信,塞進她手里,“這是我給我哥寫的,他在鐵城碼頭當搬運工,你拿著信去找他,他會先給咱們找個落腳的地方。”
信封上的字歪歪扭扭,卻用力得劃破了紙。林晚秋捏著信,指尖能摸到紙背面凸起的筆痕,像他此刻緊繃的下頜線。
船越走越遠,岸上的人影變成了小小的黑點。沈亦舟拿起船槳,一下下劃著水,晨光漫過他的側臉,把他的影子投在船板上,隨著水波晃悠。林晚秋把信小心翼翼地夾進貼身的布包,和銅船模放在一起,心里像被什么東西堵著,說不清是酸還是澀。
“冷不冷?”沈亦舟脫了外褂,披在她肩上,粗布衣裳帶著他的體溫,“過了這片河灣,風就小了。”
她搖搖頭,看著他用力劃槳的樣子,手臂上的肌肉隨著動作起伏,心里忽然定了下來。不管前面有什么,只要跟著他,好像就不怕了。
小船順流而下,晨光鋪滿水面,像撒了層碎金。林晚秋把臉貼在微涼的船板上,聽著水聲嘩嘩,忽然想起昨夜沈亦舟塞給她小刀時說的話——“有我在”。她悄悄摸了摸布包里的船模,嘴角忍不住往上揚。
可她沒瞧見,沈亦舟劃槳的間隙,回頭看了她一眼,又飛快地轉回去,喉結滾了滾,手里的槳差點打滑。他懷里還藏著封信,是給爹娘的,寫了整夜,最后只化成一句“勿念,兒會好好照顧晚秋”,卻終究沒敢塞給她,怕她看見字里的抖。
船過了河灣,風果然小了,陽光暖烘烘地曬在身上。林晚秋打了個哈欠,靠著船幫閉上眼,布包里的信硌著腰,像塊小小的石頭,卻安穩得讓人踏實。她想,等到了鐵城,第一樁事,就是把這封信親手交給沈亦舟的哥,然后,等著沈亦舟給她打銅鐲子。
卻不知那封信,后來被她壓在箱底,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直到紙頁泛黃發脆,也沒被拆開過。就像很多沒說出口的話,在時光里沉成了謎。
第三章:空蕩的渡口
卯時的露水最重,把青溪鎮的石板路浸得發亮。林晚秋站在渡口的老柳樹下,布包里的銅船模硌著肋骨,像塊冰,卻被心口的熱烘得發暖。
她來得早了些,河面上還蒙著層薄霧,遠處的蘆葦蕩在霧里晃成一片灰綠,只有偶爾掠過的水鳥,翅膀劃破霧氣,留下道轉瞬即逝的白痕。老柳樹的枝條垂到水面,沾著的露珠滴進水里,“嘀嗒”一聲,在寂靜里蕩開圈圈漣漪。
“該來了吧。”她對著水面喃喃自語,伸手摸了摸布包——里面除了船模,還有那件碎花褂子,疊得方方正正,邊角都對齊了。昨夜她幾乎沒合眼,縫補褲腳時,針腳走得比繡嫁妝還仔細,仿佛那不是去私奔,是去赴一場體面的宴席。
霧漸漸散了些,露出對岸的石階。林晚秋瞇起眼,看見石階上空空蕩蕩,只有個挑著擔子的貨郎,慢悠悠地走過,扁擔“咯吱”響著,驚飛了柳樹上的麻雀。
她心里泛起一絲慌。沈亦舟不是拖沓的性子,約定好的時辰,他總愛提前到,說“等你比讓你等好”。就像上次她去鎮上買絲線,不過遲了一刻鐘,他就沿著河岸找了半里地,見著她時,額頭的汗比她還多。
“許是被什么事絆住了。”她往手心呵了口氣,搓了搓冰涼的指尖。布包里還揣著那封沒寫完的信,“船模在,我就在”那行字被她反復摩挲,紙角都起了毛。她想,等他來了,就把信給他,看他會不會笑她矯情。
日頭慢慢爬高,霧氣徹底散了,河面亮得晃眼。老船夫撐著篙從上游過來,見她獨自站在柳樹下,喊了聲:“姑娘,等船?”
林晚秋搖搖頭,聲音有點發緊:“等個人。”
“等沈小子?”老船夫把船泊在岸邊,蹲下來卷旱煙,“那小子昨兒跟我打招呼,說今兒卯時要借船,怎么還沒來?”
她的心沉了沉,強笑著說:“許是睡過頭了。”
“他才不會。”老船夫點著煙,吸了一口,“那小子猴精,辦正經事比誰都上心。前兒還跟我打聽,說鐵城的工廠招不招女工,想讓你去了也有個活計。”
煙味混著水汽飄過來,嗆得林晚秋眼眶發熱。她別過臉,望著遠處的水天相接處,那里的云像團揉皺的棉絮,慢慢往南移。沈亦舟說過,鐵城在北邊,等他們上了船,就得朝著云飄來的方向走。
“要不,我先送你過去?”老船夫磕了磕煙灰,“他要是來了,我再回頭接他。”
林晚秋咬著唇搖頭。她不敢走,怕她剛離岸,他就氣喘吁吁地跑來,像上次找她時那樣,手里還攥著顆給她留的糖。
又等了半個時辰,河面上的船漸漸多了起來,有載貨的商船,有漁民的小漁船,唯獨沒有沈亦舟的身影。鎮上的炊煙升起來了,混著早飯的香氣,飄過河面,勾得她肚子咕咕叫,可她一點胃口也沒有。
布包里的船模越來越涼,硌得她生疼。她開始胡思亂想:是不是他家里人發現了?是不是昨夜的斗毆惹了麻煩?是不是……他后悔了?
這個念頭剛冒出來,就被她狠狠按下去。沈亦舟不是那樣的人。他說要帶她走時,眼睛亮得像星子,那眼神騙不了人。
“姑娘,要不你先回去?”老船夫收拾著篙,“這日頭都快到頭頂了,再等下去,怕是要中暑。”
林晚秋沒動。她走到沈亦舟常坐的那塊青石板旁,蹲下來,指尖撫過上面的一道刻痕——是他昨天用小刀劃的,說要做個記號,免得下次找錯地方。刻痕還很新,邊緣的碎石子硌著指尖。
就在這時,她看見石板縫里塞著個東西,是張折疊的紙,被露水浸得發潮。
她的心猛地一跳,趕緊抽出來展開。是沈亦舟的字跡,力透紙背,卻帶著點潦草,像是寫得很急:
“晚秋,等我。昨夜事出緊急,我得先避一避,去鐵城找我哥。你拿著船模等我,最多三個月,我一定回來接你。別信旁人的話,別嫁人。沈亦舟絕不負你。”
字跡的末尾,還畫了個歪歪扭扭的船,桅桿上系著根紅繩,像極了他給她的那個船模。
林晚秋捏著信紙,指腹一遍遍撫過“絕不負你”四個字,紙頁上的潮意混著她的眼淚,暈開了一小片墨痕。她忽然笑了,帶著淚笑的,像雨后的石榴花,有點澀,卻透著股韌勁。
她把信紙小心翼翼地折好,放進布包,緊貼著銅船模。然后對著河面喊:“老船夫,麻煩您送我回去吧。”
小船離岸時,她回頭望了眼渡口,柳樹的影子在水面晃啊晃,像個沒說完的約定。她知道,從今天起,她得守著這個約定,守著這只船模,等那個說“絕不負你”的人回來。
日頭升到正空,把她的影子縮成小小的一團,映在船板上,隨著水波輕輕晃,像在說:等多久都愿意。
第四章:消失的蹤跡
林晚秋是被娘的哭聲驚醒的。
她趴在老宅的八仙桌上睡著了,懷里還緊緊抱著那個藍布包。布包里的銅船模硌著肋骨,留下一道淺淺的印子,像枚沉默的印章。信紙被她壓在最底下,沈亦舟的字跡透過布層,仿佛能烙進肉里。
“你說你這孩子,怎么就這么傻!”娘的聲音嘶啞,帶著哭腔,手里的雞毛撣子舉得高高的,卻遲遲沒落下,“那沈小子是什么人?游手好閑,打架斗毆,你跟著他能有什么好!”
爹坐在旁邊的太師椅上,臉色鐵青,吧嗒吧嗒地抽著旱煙,煙鍋子敲得桌沿“篤篤”響:“我早說過,離他遠點!現在好了,人跑了,把你晾在渡口,傳出去咱們林家的臉都要被你丟盡了!”
林晚秋沒說話,只是把布包往懷里又摟了摟。她知道現在說什么都沒用,他們不會信沈亦舟的信,不會信他說的“三個月就回來”。在他們眼里,沈亦舟就是個不靠譜的混小子,而她,是個被愛情沖昏頭腦的傻瓜。
“你倒是說話啊!”娘見她不吭聲,更急了,眼淚掉得更兇,“你要是真跟他跑了,我就沒你這個女兒!”
“娘,”林晚秋終于抬起頭,聲音有點發啞,“他會回來的。”
“回來?他要是能回來,太陽都能從西邊出來!”爹猛地把煙鍋子往地上一磕,火星濺起來,“我已經托人去打聽了,昨夜他把劉三打成了重傷,劉家人已經去派出所報案了,他這是畏罪潛逃,躲還來不及,怎么可能回來!”
林晚秋的心猛地一沉。她不知道沈亦舟把人打成了重傷,信里只說“事出緊急”。她張了張嘴,想說沈亦舟不是故意的,可話到嘴邊又咽了回去。在這個節骨眼上,任何辯解都顯得蒼白無力。
接下來的幾天,青溪鎮炸開了鍋。關于沈亦舟打人跑路、林晚秋癡心等待的流言像長了翅膀,飛遍了鎮上的大街小巷。
林晚秋出門挑水,總能感覺到背后有人指指點點。
“就是她,林家的大姑娘,聽說要跟沈小子私奔呢。”
“嘖嘖,真是不要臉,沈小子都跑了,還等著呢。”
“我看啊,八成是被甩了,自作自受。”
那些話像針一樣扎在林晚秋心上,讓她渾身不自在。可她還是每天按時出門,按時挑水,按時做飯,仿佛什么都沒發生過。只是她不再去渡口了,也不再站在門口張望了,她把所有的念想都藏在了那個藍布包里,藏在了那只銅船模上。
她開始四處打探沈亦舟的消息。她去問沈亦舟的鄰居,鄰居搖搖頭,說沈家人一早也收拾東西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她去問鎮上的貨郎,貨郎說隱約聽說沈亦舟往北邊去了,但具體去了哪里,誰也說不準。
日子一天天過去,轉眼一個月就過去了。沈亦舟還是沒有消息,也沒有信寄來。林晚秋的心像被泡在冷水里,一點點變涼。
這天,林晚秋正在院子里洗衣服,老郵遞員老李忽然背著郵包走了進來。
“晚秋姑娘,有你的信。”老李把一封信遞給她,臉上帶著些同情。
林晚秋的心猛地一跳,趕緊接過信。信封上的字跡有點陌生,但寄信人地址寫的是“鐵城”。她的手忍不住顫抖起來,難道是沈亦舟寄來的?
她迫不及待地拆開信,可里面的內容卻讓她瞬間如墜冰窟。信不是沈亦舟寫的,而是沈亦舟的哥哥寫的。信里說,沈亦舟確實去了鐵城找他,但只待了幾天就又走了,說是要去更遠的地方闖蕩,讓她不要再等了,忘了他吧。
林晚秋捏著信紙,指尖冰涼。她不信,她不相信沈亦舟會這么絕情,不相信他會違背自己的承諾。一定是哪里弄錯了,一定是沈亦舟的哥哥不想讓她去找他,才故意這么說的。
“老李叔,”林晚秋抬起頭,眼里含著淚,“這封信……你確定是沈亦舟的哥哥寄來的嗎?”
老李嘆了口氣,點點頭:“沒錯,是從鐵城寄來的,地址也是對的。晚秋姑娘,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可這感情的事,強求不來。沈小子既然走了,你也該好好過日子。”
林晚秋沒說話,只是把信緊緊攥在手里,信紙被她攥得皺巴巴的。她轉身走進屋里,把自己關在房間里,抱著那個藍布包,哭了很久很久。
哭完之后,她擦干眼淚,把那封信和沈亦舟寫的那張紙條放在一起,然后小心翼翼地放進布包。她告訴自己,她還是要等,她要等沈亦舟回來,親口問他為什么。
她不知道,這一等,就是漫長的幾十年。而那個消失的蹤跡,像一顆投入湖面的石子,在她的生命里激起了層層漣漪,卻再也沒有回到原點。
第五章:銅船模的溫度
閣樓的木梯積著層薄灰,林晚秋踩上去時,梯板發出“吱呀”的呻吟,像怕驚擾了什么。她懷里抱著藍布包,包角蹭過結滿蛛網的橫梁,帶起細小的飛絮,在從窗欞漏進來的光柱里悠悠打轉。
這里是老宅最安靜的地方,除了每年翻曬冬衣,很少有人上來。梁上懸著爺爺留下的舊漁網,墻角堆著娘年輕時的嫁妝箱,鎖扣早已銹死,像封存著另一個時代的沉默。林晚秋走到最里側的角落,挪開那只裝著陳年棉絮的木箱,露出底下一方凹陷的地面——是她昨夜趁著家人睡熟,悄悄用鋤頭鑿的,土塊還帶著新鮮的濕意。
她蹲下身,把藍布包放進凹陷里。銅船模的棱角隔著布,硌得掌心發麻,像沈亦舟臨走前那句“絕不負你”,帶著不容置疑的重量。她摸出塊油紙,仔細裹住布包,又往縫隙里塞了幾把干稻草——是去年曬的,帶著陽光的味道,能防潮。
“得藏得再深些。”她對著空氣喃喃自語,指尖撫過潮濕的泥土。前幾日鎮上的三姑六婆來串門,眼睛總往她房里瞟,話里話外都在打探“沈亦舟留下的念想”。有次二嬸甚至趁她去挑水,溜進她房間翻箱倒柜,若不是娘及時撞見,那只船模恐怕早就成了街坊鄰里的笑柄。
她往凹陷里填土,土塊落在油紙上,發出沉悶的響。每填一把,心里就踏實一分,仿佛這樣就能把那些流言蜚語也埋進土里。填到與地面齊平時,她又搬回棉絮箱壓住,箱底的銅鎖“咔嗒”扣上,鎖孔里還插著半截生銹的鑰匙——是她故意弄斷的,這樣誰也打不開。
做完這一切,她靠在墻角喘氣,額角的汗滴在地板上,暈開一小片深色。閣樓里很暗,只有那束光柱里的飛絮還在飄,像無數個沒說出口的念頭。她忽然想起沈亦舟給她船模的那個夜晚,他說“這銅是老渡口沉船上拆下來的,經得住潮”,那時她只當是少年人的浪漫說辭,如今才懂,他早把“長久”二字,藏進了這冰涼的銅里。
下樓時,正撞見弟弟林德明背著書包從外面回來。他今年十五,眉眼間已經有了爹的硬朗,見著林晚秋從閣樓下來,皺了皺眉:“又往樓上跑什么?娘說你這幾日魂不守舍的。”
“翻點舊衣裳。”林晚秋避開他的目光,往自己房間走。自沈亦舟走后,這弟弟就像爹的影子,看她的眼神里總帶著點“恨鐵不成鋼”的銳利。
“別再想那個沈亦舟了。”林德明在她身后喊,聲音不大,卻像塊石頭砸在地上,“劉三他爹昨天還來咱家,說要不是你勾著他,他兒子也不會被打成那樣。”
林晚秋的腳步頓住了,指尖在袖口里攥成拳。她沒回頭,只是低聲說:“他不是那樣的人。”
“不是?”林德明追上來,擋在她面前,“人都跑了,把爛攤子扔給你,這就是你說的‘不是那樣的人’?我告訴你姐,爹已經托媒人給你尋了戶好人家,是鄰鎮做綢緞生意的,家底殷實,下個月就來相看。”
“我不嫁。”林晚秋的聲音發顫,卻帶著股犟勁,“我等他回來。”
“等?等他回來蹲大牢嗎?”林德明的聲音拔高了,“劉家人已經把狀子遞到縣里了,說要抓他去判刑!你還等?”
這話像把冰錐,狠狠扎進林晚秋心里。她后退一步,撞在門框上,后腰正抵著那根凸起的木棱,疼得她倒吸一口冷氣。原來他不只是“避一避”,是真的惹下了天大的麻煩。
那天下午,林晚秋躲在房間里,沒去灶房幫忙。她坐在床沿,反復摩挲著袖口——那里沾著點閣樓的土,帶著銅船模的涼味。窗外的石榴樹被風吹得嘩嘩響,像有人在外面哭。她忽然想起沈亦舟說過,銅這東西,越摸越暖,就像人心,只要不涼透了,總有熱起來的一天。
傍晚時分,老郵遞員老李敲開了林家的門。他沒像往常那樣把信遞到堂屋,而是悄悄拉著林晚秋走到院角的石榴樹下,從郵包最底層摸出個皺巴巴的信封。
“這信……地址寫得潦草,收件人是你。”老李的聲音壓得很低,眼角的皺紋擠在一起,“寄信人沒寫名字,只在郵票旁邊畫了個小船。”
林晚秋的心跳瞬間提到了嗓子眼。她接過信封,指尖觸到紙面上凹凸的紋路,果然在右上角看到個小小的船形印記,桅桿上還歪歪扭扭畫著根紅繩。
“老李叔,謝謝您。”她把信緊緊攥在手里,指節都泛了白。
“看看吧,看完了……別太較真。”老李嘆了口氣,背著郵包走了,腳步在青石板上敲出“篤篤”的響,像在替她嘆氣。
林晚秋躲回房間,反鎖上門,才敢拆開信封。里面只有一張薄薄的紙,字跡倉促,墨痕都有些暈開,卻分明是沈亦舟的筆體:
“晚秋,勿念。已到鐵城,一切安好。等我。”
沒有多余的話,沒有解釋,甚至沒說歸期。可林晚秋捧著那張紙,卻像捧著團火,燙得指尖發麻,眼眶卻熱了。她把信紙折成小小的方塊,塞進貼身的口袋里,貼著心口的位置。
夜深人靜時,她又爬上閣樓。借著從窗洞鉆進來的月光,她跪在棉絮箱前,伸手撫摸著箱底的銅鎖。鎖孔里的半截鑰匙在月光下泛著微光,像顆不肯熄滅的星。
“我就知道你會來信。”她對著木箱輕聲說,聲音輕得像嘆息,“他們說你會蹲大牢,說你不會回來,可我不信。你說過,船模在,你就在。”
她伸出手,掌心貼著冰涼的木箱,仿佛這樣就能摸到油紙底下的銅船模。那銅的溫度,透過層層阻隔滲過來,混著她掌心的汗,竟真的有了點暖意。
那晚,林晚秋沒回房睡,就靠在棉絮箱旁,聽著閣樓外的風聲,像聽著遙遠的船鳴。她知道,只要這銅船模的溫度還在,她的念想就不會涼,等下去的勇氣,也就不會散。
第七章:舊信里的破綻
秋雨連下了三天,青石板路上積著水洼,倒映著灰蒙蒙的天。林晚秋坐在窗邊繡著鞋面,針腳卻總也扎不準——案頭那封信已經放了兩天,信封上的郵戳是省城的,寄信人欄只畫了個小小的船錨,是沈亦舟的記號。
她捏著信紙的指尖微微發顫,展開時,墨跡被雨水洇過的地方有些模糊,卻能看清那熟悉的字跡:“晚秋,勿念。我在南邊安好,待風聲過些便回。另,劉三之事,有證人愿出面作證,勿憂。”
短短幾行字,她卻看了不下二十遍。
“娘,亦舟來信了!”她揚聲喊,聲音里帶著壓抑不住的雀躍。娘從灶房探出頭,手里還拿著鍋鏟:“他說啥了?啥時候回?”
“他說在南邊安好,還說劉三的事有證人……”林晚秋把信遞過去,嘴角止不住地上揚,“我就說他不會有事的!”
娘接過信,眉頭卻越皺越緊,反復看了幾遍,忽然嘆了口氣:“晚秋,你再仔細看看這信。”
“怎么了?”林晚秋心里一沉,湊過去重新讀。沈亦舟的字向來挺拔,撇捺間帶著股勁兒,可這封信上的筆畫卻有些發飄,尤其是“南邊”兩個字,捺腳收得格外倉促,不像他平日的風格。
“你看這船錨,”娘指著信封上的記號,“亦舟畫船錨,總愛在錨鏈上多畫兩圈,說這樣‘錨得牢’,你再看這個——”她指尖點著那個潦草的船錨,“鏈環稀稀拉拉,倒像是……故意模仿的。”
林晚秋的心猛地往下墜。她確實記得,沈亦舟畫船錨時總較真,說“細節見心意”,絕不會畫得這么敷衍。可……除了他,誰會知道這個記號?
“還有這紙,”娘摸著信紙邊緣,“是省城‘文墨齋’的專用紙,亦舟向來只用鎮上‘老記’的粗紙,說那紙吸墨,寫著順手。他哪會突然換紙?”
疑點像雨后的蘑菇,一個個冒出來。林晚秋捏著信紙,指腹蹭過“證人”兩個字,忽然想起沈亦舟臨走前說的話:“劉三那幫人,跟縣里的李科長沾親帶故,硬碰硬討不到好,只能先避避。”若真有證人,他何必跑得那么急?
“會不會是……他急著寫信,沒顧上這些?”她還想替他辯解,聲音卻沒了底氣。
娘把信折好,塞進她手里:“你自己拿主意。但晚秋啊,人心隔肚皮,尤其是這種時候,多留個心眼總沒錯。”
林晚秋把信揣進貼身的口袋,指尖能摸到信紙的褶皺。窗外的雨還在下,敲打著窗欞,像在提醒她什么。她走到院角,看著那片埋著石榴籽的土地,泥土濕漉漉的,連個嫩芽的影子都沒有。
“你到底在哪?”她對著泥土輕聲問,“這信……是你寫的嗎?”
傍晚時,林德明從鎮上回來,進門就喊:“姐,我聽說沈亦舟在省城被抓了!說是有人看見他在碼頭跟人打架,把對方胳膊打斷了!”
林晚秋手里的繡花針“啪嗒”掉在地上:“不可能!他剛來信說在南邊安好……”
“信?什么信?”林德明湊過來,“我下午去郵局寄東西,聽張嬸說,昨天有個穿黑褂子的男人去寄信,問他寄給誰,他支支吾吾的,地址寫的就是咱家,還畫了個歪歪扭扭的船錨——那男人根本不是沈亦舟!”
林晚秋的臉瞬間白了。她猛地掏出那封信,反復看著那潦草的船錨,忽然想起沈亦舟說過,他的船錨記號,只有他和他爹會畫,可他爹去年就過世了。
“是圈套……”她喃喃自語,指尖冰涼,“有人想引我去找他,或者……想讓我以為他真的出事了。”
林德明皺眉:“誰會這么做?”
“劉三的人?”林晚秋攥緊信紙,指節泛白,“他們想讓我亂了陣腳,或者逼亦舟現身?”
雨還在下,院角的泥土里,石榴籽安靜地躺著,像在等待一個真相。林晚秋忽然站起身,把信揣好:“我要去省城。”
“你瘋了?”林德明拉住她,“現在去就是自投羅網!”
“我不去找他,”她眼神亮得驚人,“我去‘文墨齋’問問,是誰買了這紙,又是誰寄了這封信。亦舟沒說假話,那這信就是假的;他若說了假話……”她頓了頓,聲音發顫,卻帶著股狠勁,“我也要弄明白,他為什么要騙我。”
娘從屋里出來,手里拿著個布包:“帶上這個,是你爹以前跑商時用的路引,或許能用上。路上當心,別信任何人。”
林晚秋接過布包,指尖觸到里面硬硬的東西,是娘偷偷塞的銀圓。她回頭望了眼那片埋著石榴籽的土地,心里默默說:等我回來,咱們一起等發芽。
雨幕中,她的身影很快消失在巷口,像片被風吹走的葉子,帶著孤勇,朝著未知的方向飄去。
第八章:文墨齋的線索
省城的雨比鎮上密,林晚秋撐著油紙傘,鞋尖很快就沾了泥。文墨齋在一條老巷深處,門楣上的“文墨齋”三個字被雨水沖刷得發亮,透著股陳年的墨香。
她收了傘,站在屋檐下輕輕拍了拍衣角的水珠。推門時,風鈴“叮鈴”響了一聲,店里只有一個戴眼鏡的掌柜,正低頭用軟布擦拭一支玉筆。
“姑娘要點什么?”掌柜抬頭,鏡片后的眼睛打量著她。
“我想問一下,”林晚秋從懷里掏出那封信,“這種信紙,最近有人買過嗎?”
掌柜接過信紙,指尖捻了捻:“這是我們店里特供的‘云紋紙’,不貴重,但買的人不多,都是熟客。”他頓了頓,忽然笑了,“哦,前天倒是有個生客買過,說是要寄封重要的信,特意挑了這紙,還問我哪種墨水干得快。”
“那人長什么樣?”林晚秋的心提了起來。
“中等個頭,穿件黑褂子,臉上有道疤,在左眉骨那兒。”掌柜回憶著,“說話有點結巴,不像本地人。”
左眉骨有疤?林晚秋愣了愣——沈亦舟臉上干干凈凈,從來沒什么疤。看來那封信果然是假的。
“他還問了什么?”
“問鎮上的林晚秋住在哪,我說不知道,他就沒再問了。”掌柜把信紙遞回來,“姑娘,這信有問題?”
“沒、沒什么,”林晚秋慌忙收起信,“多謝掌柜。”
轉身出門時,風鈴又響了。她剛走到巷口,就見兩個穿黑褂子的人靠在墻根,眼神直勾勾地盯著她。左眉骨有疤的那個,正慢悠悠地用手指摩挲著疤,嘴角掛著笑。
林晚秋的心猛地一沉,轉身就往文墨齋跑。剛要推門,手腕卻被抓住,力道大得像鐵鉗。
“林姑娘,別來無恙啊。”疤臉男人笑得陰惻惻,“沈亦舟那小子跑了,我們找不著他,只好找你聊聊了。”
“我不認識你!”林晚秋掙扎著,傘柄在手里攥得發白。
“不認識?”男人猛地把她往巷子里拽,“那就去個認識的地方好好想想!”
巷子里陰暗潮濕,墻角堆著發霉的雜物。林晚秋被推搡著撞到墻上,后腰磕在磚頭上,疼得她倒吸一口冷氣。
“說!沈亦舟藏哪了?”疤臉男人逼近一步,唾沫星子噴在她臉上。
“我不知道!”林晚秋咬著牙,死死盯著他,“你們是誰?為什么要冒充他寫信?”
“冒充?”男人愣了一下,隨即大笑,“那蠢小子哪配我們冒充?實話告訴你,他早被我們抓住了,現在怕是……”
話沒說完,巷口忽然傳來一聲怒喝:“放開她!”
林晚秋抬頭,看見沈亦舟穿著件洗得發白的短褂,手里攥著根木棍,額角還滲著血,眼神像要吃人。
“沈亦舟!”疤臉男人眼睛一亮,“來得正好!省得我們費勁找了!”
沈亦舟沒說話,一木棍就朝疤臉男人揮過去。那男人慌忙躲開,另一個黑褂子立刻撲上來,三人扭打在一起。沈亦舟顯然是受了傷,動作有些遲緩,肩膀挨了一拳,悶哼一聲,卻反手一棍打在對方膝蓋上,疼得那人嗷嗷叫。
林晚秋撿起地上的碎磚塊,趁著疤臉男人轉身的瞬間,狠狠砸在他背上。
“嗷!”男人吃痛,轉身瞪她,沈亦舟抓住機會,一棍擊中他的側臉,疤臉男人晃了晃,癱倒在地。
巷子里終于安靜了,只有粗重的喘息聲。沈亦舟捂著肩膀,額角的血滴在衣領上,像開了朵小紅花。
“你怎么來了?”他聲音沙啞,帶著后怕。
“我再不來,就要被你的‘信’騙死了!”林晚秋眼眶一熱,眼淚差點掉下來,“你沒事吧?”
沈亦舟咧嘴笑了,露出顆小虎牙:“沒事……就是有點想你。”
雨還在下,打濕了他的頭發,卻擋不住眼里的光。林晚秋忽然覺得,這省城的雨,好像也沒那么冷了。
第九章:叛逆的闖入者
2015年的青溪鎮,夏末的蟬鳴還拖著冗長的尾音,林曉星拖著行李箱,一腳踹開老宅那扇掉漆的木門時,正撞見林晚秋蹲在石榴樹下,用軟布擦拭著什么。
“奶,我回來了。”她把行李箱往廊下一扔,發出“哐當”一聲悶響,震得檐角的蛛網抖落幾片灰塵。
林晚秋沒回頭,指尖依舊在那物件上細細摩挲,陽光透過石榴葉的縫隙落在她手上,能看見皮膚下凸起的青筋。“回來了。”她的聲音像老宅的木門,帶著常年不開的滯澀。
林曉星撇撇嘴,踢掉帆布鞋,赤腳踩在冰涼的青石板上。這老宅她從小就不愛來,一股子霉味混著老人味,墻角的蛛網結了又結,奶奶從不肯讓人打掃,說“這是念想結的網”。她尤其受不了奶奶這副樣子——永遠對著些舊物件發呆,仿佛整個世界就剩她和那些落灰的破爛。
“我爸讓我問你,國慶節去不去城里住幾天?我媽說給你換了臺新電視,能看一百多個臺。”她靠在門框上,刷著手機,屏幕的光映在她涂著亮粉色指甲油的指尖上。
林晚秋終于放下手里的東西,是個用紅布裹著的木盒,邊角磨得發亮。“不去。”她站起身,往堂屋走,背影佝僂著,像株被秋霜打蔫的蘆葦,“城里太吵,睡不安穩。”
“吵?這里才悶得讓人發瘋!”林曉星收起手機,聲音拔高了些,“你看看這房子,墻皮都掉了,電線老化得能著火,我爸說了,要么你去城里,要么我們就把這老宅翻新了!”
“不準動!”林晚秋猛地回頭,渾濁的眼睛里難得有了點光,像被踩了尾巴的貓,“這是我的家,動了就不是原來的樣子了!”
“原來的樣子有什么好?”林曉星嗤笑一聲,“除了這些破爛,還有什么?我長這么大,就沒見過我爺爺,你也從不跟我們說,我爸說你心里藏著個死人,比親孫子還重要!”
這話像根針,狠狠扎進林晚秋心里。她的嘴唇哆嗦著,想說什么,最終卻只是轉身進了堂屋,“砰”地關上了房門。
林曉星對著緊閉的房門做了個鬼臉,轉身去了后院。她記得閣樓里堆著些舊書,或許能翻出點有意思的東西——她才不信奶奶那些“念想”有多金貴,多半是些不值錢的老掉牙物件。
閣樓的木梯比記憶里更晃,每踩一步都發出“吱呀”的哀鳴。林曉星扶著積灰的欄桿往上爬,鼻腔里灌滿了灰塵和霉味,嗆得她直皺眉。閣樓里果然堆著不少東西:褪色的綢緞被面、缺了口的青花瓷碗、還有幾捆用麻繩捆著的舊書,書脊上的字早就模糊不清。
“什么破玩意兒。”她踢了踢腳邊的木箱,箱子沒鎖,被她踢得敞開一條縫。
好奇心驅使她蹲下身,伸手往里掏了掏。指尖觸到一片冰涼的金屬,她猛地一拽,帶出個藍布包,布面早就洗得發白,邊角磨出了毛邊。
打開布包的瞬間,林曉星愣住了。里面裹著個巴掌大的銅船模,船身刻著細密的水波紋,桅桿上系著根褪色的紅繩,雖然蒙著層灰,卻依舊能看出當年的精致。船模底下壓著幾張泛黃的信紙,還有一張邊角卷曲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年輕姑娘梳著兩條麻花辮,眉眼清亮,身邊站著個穿白襯衫的少年,咧嘴笑著,露出兩顆小虎牙,兩人身后是條泛著光的河,岸邊的柳樹垂著綠絲絳。
“這是……奶?”林曉星捏著照片,指尖有些發顫。她從沒見過奶奶年輕時的樣子,更不知道她還有這樣笑靨如花的時刻。
她拿起最上面的信紙,字跡遒勁有力,帶著股少年人的張揚,開頭寫著“晚秋親啟”,末尾的署名是“沈亦舟”。
“沈亦舟?”林曉星念叨著這個名字,心里咯噔一下——這個名字她似乎在哪聽過,好像是爺爺去世后,有次親戚閑聊,說奶奶年輕時有個“沒成的”,就叫這個名字。
她飛快地往下讀,信里寫著“待我在鐵城站穩腳跟,便回來接你”“船模為信,此心不渝”,字里行間的熾熱幾乎要燒穿紙頁。林曉星的心越跳越快,她又拿起另一張紙,是張揉得皺巴巴的火車票,出發地是“青溪鎮”,目的地是“鐵城”,日期是1978年的秋天。
“鐵城……”她喃喃自語,忽然想起什么,翻出手機搜索“鐵城 1978 工廠”,屏幕上跳出一堆關于北方工業城市“鐵城”的舊聞,其中一條提到“機床廠”時,她的目光頓住了——信里沈亦舟說過,他要去鐵城的機床廠找表哥。
閣樓的窗沒關,風灌進來,卷起幾張信紙,其中一張輕飄飄落在她腳邊。她撿起來,看見背面用鉛筆寫著個地址:鐵城機床廠宿舍區,王秀蓮收。字跡娟秀,和沈亦舟的筆體截然不同。
“王秀蓮是誰?”林曉星皺起眉,把所有東西重新裹進藍布包,緊緊抱在懷里。她忽然覺得,這個沉悶的老宅里,藏著一個她從未了解過的奶奶,和一段被時光塵封的故事。
樓下傳來開門聲,林晚秋的腳步聲慢慢靠近樓梯口。林曉星慌忙把布包塞進背包,拍了拍身上的灰,裝作若無其事地往下走。
“在上面瞎翻什么?”林晚秋的目光落在她背上的包上,帶著審視。
“沒什么,找本書看。”林曉星避開她的視線,快步往門口走,“我去鎮上買點吃的,中午不回來吃了。”
她幾乎是逃也似的沖出老宅,陽光刺得她眼睛發花。懷里的背包沉甸甸的,像揣著個滾燙的秘密。她摸出手機,翻到通訊錄里“老郵遞員李爺爺”的名字——小時候爺爺帶她去郵局寄信時,認識的那個老李叔,他在青溪鎮待了一輩子,說不定知道些什么。
電話撥通的瞬間,林曉星聽見自己的心跳聲,像敲在老宅的青石板上,篤篤作響,帶著一種前所未有的沖動。她要去鐵城,要去弄清楚,這個叫沈亦舟的人,到底和奶奶有著怎樣的過往。
第十章:老李的遺言
鎮衛生院的消毒水味,混著窗外飄來的桂花香,在走廊里纏成一股古怪的味道。林曉星攥著手機,站在病房門口,透過門上的玻璃,看見老郵遞員老李躺在病床上,臉頰陷得厲害,呼吸像破風箱似的,每一次起伏都帶著艱難的停頓。
“進來吧,他剛醒。”護士端著托盤走過,替她推開了門。
林曉星放輕腳步走到床邊,老李的眼睛半睜著,渾濁的眼珠轉了轉,落在她身上時,忽然亮了點。“是……曉星丫頭?”他的聲音氣若游絲,手在被單上摸索著,像是在找什么。
“李爺爺,是我。”林曉星握住他枯瘦的手,那手上布滿老年斑,指關節因為常年握郵包而變形,“我來看您了。”
老李的手顫巍巍地回握她,力道輕得像片羽毛。“你奶奶……她還好嗎?”
“挺好的,還在老宅住著。”林曉星避開他的目光,指尖無意識地摩挲著背包帶——里面的藍布包硌著腰,像塊燒紅的烙鐵。她來之前打了腹稿,想旁敲側擊問問沈亦舟,可真站到老李床前,那些話卻堵在喉嚨口,怎么也說不出來。
老李咳了兩聲,護士進來替他掖了掖被角,低聲說:“老人家這幾天就靠吊著一口氣,你們有啥話,趕緊說。”
病房里又靜下來,只有墻上的吊瓶“滴答”作響,像在數著剩下的時間。老李忽然偏過頭,看著林曉星:“丫頭,你是不是……找到什么了?”
林曉星的心猛地一跳,抬頭撞見他了然的眼神,那眼神里沒有驚訝,只有一種“該來的總會來”的平靜。她咬了咬唇,從背包里掏出那個藍布包,放在床頭柜上,沒打開,只是輕聲問:“李爺爺,您認識沈亦舟嗎?”
老李的目光落在布包上,嘴角牽起一抹極淡的笑,像水面上的漣漪,轉瞬即逝。“認識……怎么不認識。”他的聲音飄得很遠,像是沉進了回憶里,“那小子,當年可是青溪鎮最野的崽,爬樹掏鳥窩,下河摸魚蝦,樣樣在行,可他對晚秋姑娘……是真上心。”
林曉星屏住呼吸,聽他繼續說。
“1978年秋天,他跟晚秋姑娘約好要走,頭天夜里為了幫鄰居討工錢,跟劉三那幫人打起來,失手把人打傷了。”老李的喉結滾了滾,呼吸更急了,“他怕連累晚秋,沒敢去渡口,讓我把船模和信帶給她,說自己先去鐵城避避,站穩了就回來接她。”
這些和布包里的信對上了。林曉星追問:“那他后來回來了嗎?”
老李搖了搖頭,眼里泛起水光:“他走的時候,我去送的。在碼頭偷偷上的貨船,懷里揣著晚秋姑娘繡的平安符,說‘等我回來’。”他頓了頓,忽然劇烈地咳嗽起來,咳得臉都紅了,護士趕緊過來給他順氣。
等咳嗽平息,老李的聲音更弱了,他抓著林曉星的手,指腹在她手背上反復摩挲,像是在確認什么。“他沒回……但他沒死。”
“您怎么知道?”林曉星的心跳得像擂鼓。
“我送信跑遍了周邊市縣,1980年春天,在鐵城的機床廠門口,遠遠看見過他一次。”老李的眼睛望著天花板,像是在描摹那個遙遠的身影,“他瘦了,穿著工裝,胳膊上纏著繃帶,跟一個女工說著話,笑得挺開心……可他沒看見我。”
林曉星想起那張模糊的火車票,1980年青溪到鐵城,原來他真的去了那里。“那您為什么不告訴我奶奶?”
“告訴他啥?”老李苦笑,“說他在鐵城有了新歡?晚秋那時候剛從鬼門關走一遭回來,身子骨弱,我哪敢再刺激她。”他忽然湊近,聲音壓得極低,“而且……我看見他的時候,他跟人打招呼,人家喊他‘陳建國’。”
“陳建國?”林曉星愣住了,“他改名字了?”
“八成是怕被人認出來。”老李的手開始發涼,眼神也漸漸渙散,“丫頭,那包東西……是他留下的吧?”
林曉星點點頭,打開布包,露出那只銅船模。陽光透過窗戶照在銅面上,映出細碎的光斑,像撒了把星星。
老李的眼睛亮了亮,伸出手想摸,卻在半空中停住,又無力地垂落。“船模……他說這是祖傳的,能鎮災。他讓我跟晚秋說,船模在,他就在……”他的聲音越來越輕,“我藏了幾十年,總覺得該告訴你奶奶,又怕她……”
“怕她難過?”林曉星替他說了后半句。
老李沒回答,只是望著船模,喃喃自語:“他在鐵城……機床廠……王秀蓮……”這幾個詞斷斷續續的,像散落在地上的珠子。
林曉星忽然想起信背面那個娟秀的地址——鐵城機床廠宿舍區,王秀蓮收。難道那個和沈亦舟說話的女工,就是王秀蓮?
“李爺爺,王秀蓮是誰?”
老李的嘴唇動了動,沒發出聲音。他的呼吸越來越微弱,眼睛慢慢閉上,手卻緊緊攥著林曉星的指尖,像是要把最后一點力氣都傳遞給她。
“他還活著……去鐵城……找……”
最后一個字沒說出來,他的手猛地一松,垂落在被單上。墻上的吊瓶還在“滴答”響,可病房里的呼吸聲,只剩下林曉星自己的了。
護士進來檢查了一番,輕輕嘆了口氣:“節哀。”
林曉星站在原地,手里還殘留著老李的余溫,心里卻空落落的。她把銅船模重新裹進藍布包,緊緊抱在懷里。老李的話像把鑰匙,打開了塵封的門——沈亦舟沒死,他在鐵城,改名叫陳建國,還認識一個叫王秀蓮的女人。
走出衛生院時,夕陽正把青溪鎮的屋頂染成金紅色。林曉星抬頭望了望老宅的方向,那里的煙囪沒冒煙,像個沉默的問號。她忽然做了個決定:她要去鐵城,帶著這只船模,找到那個叫“陳建國”的人,不管他是不是沈亦舟,都要問清楚當年的事。
她掏出手機,訂了第二天去鐵城的火車票。訂單確認的那一刻,她仿佛聽見老李的聲音在風里說:“去吧,丫頭,把該了的,都了了。”
背包里的銅船模,隔著布傳來冰涼的溫度,卻奇異地讓人安心。林曉星握緊背包帶,快步往鎮上的車站走去,影子被夕陽拉得很長,像條通往過去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