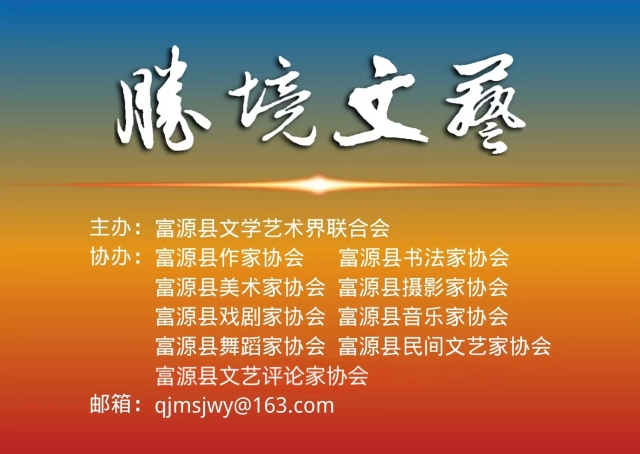棕木
天空安靜,棕樹已挨過不可數(shù)計(jì)的刀痕,
父親忍受著螞蟻,砍去它的葉部,
收獲鮮嫩的籽實(shí)。美好的繩梯上苔類蔓延,
多標(biāo)直的樹啊,苦澀的生命與愛情,
在鄉(xiāng)下竟都樂于豐產(chǎn),以此安慰崇高的明月。
又有一些可悲,敢于登高的人少了,
懸空的心就像草木在神靈的懷抱中蹙動,
我們披著蓑衣走在田野,并用棕葉捆秧苗,
這些枯槁之物變得永恒,包括我童年時(shí)
因落水而搭建的木橋。指路碑有作痛之感,
此去十里,我能遇見種滿棕木的村莊,
知我的單薄,刻我的悼辭,如同一束集句里,
深邃的傷疤。而我的父親突然衰老,
幾枚褐色種子垂落,往生般接受著相同的宿命。
清明
雨水和烏鴉很純粹,沒有仇人,
不曾誣陷我偷過他們的玉米。墓地間,
他們兀然落下,結(jié)群的小人物般,
擊穿姣好的楊花,仿佛明代時(shí),
最世俗的雜劇,依舊雅化了一場風(fēng)月。
我們本來詼諧,口含火石,
不斷在陽光中汽化著身體的溫度。
最好翻出陳舊的骨頭和銀器,
春天將要離去,還能看見什么在閃爍?
已有的迷宮與魔方,此刻不能轉(zhuǎn)喻,
荒野中,沒有人反復(fù)修改墓志,
我不能贊美,蝸牛、群山,
生長著的帶毒之物。唯一的獻(xiàn)祭之法,
啞著嗓子從時(shí)間里越出,消滅赤裸的感官。
木昌
月光下插秧的中年男人,多年后死于營養(yǎng)不良,
他的枇杷又一次成熟,鳥雀結(jié)群飛來,
在世間賴活,如我這樣的無奈之客。
我所認(rèn)識的悲劇人物不多,虱子或蚊子,
搖晃著他們的耳朵,他們的心
不知道他們的腳將要落到哪里。沒有可憎的,
一陣疼痛急切,已替代動畫片的完結(jié),
茶葉的沉垢裹挾了苦修的生命。
我們還能在河水里清洗靈魂嗎?泥沙抵達(dá)踝部,
墓碑附加于你的山野。夜色樸素,
好像你的牙縫里咀碎的紅薯,你剛借到鐵犁,
回家燃起了火塘。很多東西陳舊發(fā)霉,
你也變得無比荒涼。此刻,你的院子里,
夏天來了,我是唯一紀(jì)念你的人。
軸承
志書不會詳細(xì)記載,一個山村如何被敵人掃蕩,
也未解答一截飛機(jī)軸承為何變成殺人利器。
紀(jì)念館外,小葉女貞正在發(fā)芽,
螞蟻的王國堆聚起熾熱的碑碣。雨聲曳曳,
閉藏了明代的銅鐘,來鳳山與龍川江,
乘象之國是古老美好的機(jī)械,
藤類從其中長出,帶有堅(jiān)韌的清香。
群山如駝峰,在邊陲,我不斷仰望,
飛機(jī)過后云層的變化,并從戰(zhàn)場遺址的碉堡上,
俯視茶馬古道。這里沒有盡頭,齋公不施舍了,
雪水帶有的慈悲,早將血色洗濯。
祖父曾提起在江邊被打死的異國之?dāng)常?img class="ProseMirror-separator" alt="" width="100%" height="auto" src=""/>
而多年后我想到鎖在展柜里的慰安婦印章與面扇,
我的故鄉(xiāng)就充滿濃郁的暮色,且在歷史里運(yùn)行不止。
霧中
蕨類在露水中愈合折斷的傷口,
一只蟋蟀幸存于碾輪之下,它臃腫的尾部
從碎石間跨越,世界的中心就此偏移。
我謹(jǐn)慎地為一個中年男人刮痧,
霧氣覆蓋泛紅的肩胛,這一日,
我們將要推平所有成熟的野櫻桃和樹莓。
陽光是天空的漏洞,我的喉嚨中冷卻的烙鐵,
同樣有著腥味。曠野中,生命沒有定量,
石頭在褐土下得到護(hù)佑,飄落的氫氣球暫歇而已,
我不能抒情,萬物逐漸變得客觀,
如同仙人掌退化的刺尖,被觸碰而疼痛。
還要伸出手尋找什么?身體局限于方寸,
那么潔凈,霧與霧孿生,一聲鳥鳴將我分割,
讓我知道另外的孤島從何處抵近,繼而共存。
晚晴
焚燒麥秸的煙霧彌漫在河灣,椋鳥的聲音急促,
長歌之人不可在鄉(xiāng)間小隱,采薇的心愚笨而酸澀。
多年間我們堅(jiān)忍于此,田野下陷,身體懸空,
父親被鋤頭挖傷的腳趾,血液與污泥混融,
他不斷新添傷口,卻從未成為怨士。
塵芥更加微渺,苦蕎還不能收割,
我的味覺在春末近于塌敗,舌苔之上,
灰郁著無限的孱弱。穿過河流,
一種渾濁中,暮光打落在我們蒼頹的面龐,
生命已沒有余興,傍晚久不歸家的人,
小心翼翼,將流水積壓在眼眸里。
隔岸借問,什么是幸福?突然暴露的蟬鳴,
讓我想起醉酒的祖父,他無法怨憎這種雜亂了,
天完全黑下來,世界依舊在我們豢養(yǎng)的爐火里明亮。
舊物
還不能用喜歡的方式,度過此生,
永恒的迷茫者,安靜地坐在故鄉(xiāng)的水井邊,
沒有詩人吟詠過這里的柳樹,他們面臨衰老,
肉體與思想拆卸得只剩下乏感的部分。
如同沙發(fā)內(nèi)部的彈簧,破損的沙漏,
萬物純粹,都已失聲。教我抽煙的女人,
她的銀飾沒有光澤,不再討論糧食與敵敵畏,
一種可怕的倒生刺橫透于生命中,
像父親的短鋸,磨損嚴(yán)重,這也真的舊了。
不敢照鏡子,我的倒影是失重的鼓面,
在對峙中悸動,始終難以返去回音。
我的眉毛總掉落,我承認(rèn)浪費(fèi)時(shí)間是罪過,
于是危樓之間,我很少仰望天空,
以此掩蓋我的痛苦。
荒野
蟲類無知,荒原里的瓷片割傷我的手指,
完整的月光從露水中孽生,
我是這世上失敗的采詩官,寡淡且不神圣。
背草回來的男人,我曾答應(yīng)帶給他一株糯米香茶,
卻又食言了,提起往事,許久也記不起來,
多年前,我們遇到過同樣憂郁的蛇,
沿著小路漫游,萬物不應(yīng)該象征,
而我只是戴著眼鏡的假詩人,抒情與夢囈,
猶如他的黑鍋爐在空曠地沸熱。
他的兒子無畏于世界混沌,像個披蓑衣的隱士,
我們曾如此打扮在雨中追白鷺,直到滿身泥濘。
他的妻子出車禍死了,栗子樹亭蓋于墳頭,
悲哀的刺球依舊深扎著這個膽小的女人。莫名惶恐,
現(xiàn)實(shí)與回憶的縫隙間,我終究是不能過多言語。
花圃
有些植物,無須計(jì)較觀賞之美,
重樓與草珊瑚在瓦礫間稚嫩地長著,
味苦而性寒,不在春天出賣自己的花腔。
我沒有情懷,如同蟲類爬進(jìn)佛手柑的刺叢中,
一滴露水重新確認(rèn)塵埃的新舊。
這里離熱帶太遠(yuǎn),桂樹枝葉阻絕著陽光落下,
唯有雨水讓我打開竹籬,把芒果核扔進(jìn)花圃,
時(shí)間滋生美麗的斑點(diǎn),我該如何呻吟,
雜草艱難生存的時(shí)刻,生活是孤獨(dú)的,
村莊的左足被蘸了生根粉,
一顆稻谷長了出來。我們的院落,
麻雀光顧以后,還殘存著許多種子,
如此珍貴,我多希望它們都帶有毛刺,
擊破受縛于方寸的消逝,統(tǒng)一螽斯的喑啞。
小橋
河邊,一只貍花貓倏然跑過橋去,
然后從薺菜間謹(jǐn)慎地回過身來,睥睨著流水的輪轉(zhuǎn)。
我始終在宿命里,不得豁免,
只有沙粒在腳下逃逸,這種指路碑式的延伸,
就像多年前我在此處落水,需要喊魂,
父親搭的棕木腐爛了,神不再引領(lǐng)我,
蔥郁而溫馴的野姜或許替代著曾經(jīng)的姑且。
懸空的危險(xiǎn),柳樹未垂落于夕陽的平面,
蟬鳴之時(shí),居住在河灣的人們還沒有洗去滿身泥濘,
有人和我說青蛇出沒了,夏天,她總是憂心,
無數(shù)的蕁麻覆蓋著她的菜園,更多的冒犯被突出。
我在假想,知天命以后應(yīng)該沒有什么畏懼,
石頭頑忍,貓與蛇不會相遇,我走上搖晃的木橋,
重復(fù)十年前的招魂,母親著急地吻我的額頭。
來源:野草守望者
編輯:詹宇涵
審核:盧志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