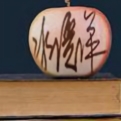鄭州行吟
#創(chuàng)作挑戰(zhàn)賽十一期#
這聲音是從哪里來(lái)的呢?它不尖銳,也不高亢,只是沉沉地、固執(zhí)地透過來(lái),像是從一本蒙塵的舊書冊(cè)里偶然抖落的一個(gè)音符,帶著隔世的恍惚。我凝神再聽,夜卻恢復(fù)了它的原樣,靜默得像一池深潭。我這才恍然,自己是在鄭州了。這念頭一生,心里便無(wú)端地浮起那后面的句子來(lái):
至今還不知道鄭州的甫曉,
胭脂搽在誰(shuí)的臉上。
這真是有些奇兀的想頭。在這座以“商都”為底色的城市里,在鋼筋與玻璃構(gòu)筑的叢林間,怎么會(huì)想起“胭脂”這般嫵媚、這般古典的詞呢?然而它一經(jīng)浮現(xiàn),便盤桓不去了。我踱到窗前,掀開簾子的一角。外面是疏疏朗朗的燈火,勾勒出樓宇沉默而堅(jiān)硬的輪廓。那胭脂,是搽在誰(shuí)的頰上了?是那位名喚“管城”的古老都邑,在三千六百年的風(fēng)霜后,于無(wú)人窺見的靜夜里,偷偷對(duì)鏡理妝,為自己覆上一層薄薄的、屬于現(xiàn)代的嫣紅么?我不知道。這謎一樣的句子,倒為這中原的夜晚,平添了幾分不可解的溫柔。
我的思緒,便不由得被這“胭脂”二字,牽著向更遠(yuǎn)的時(shí)光里走去了。那該是二十六年前了。我也是在這樣一個(gè)微涼的季節(jié)里,第一次踏上這片被稱為“河之南”的土地。那時(shí)的我,還是一個(gè)青澀的學(xué)子,懷著一顆懵懂而熱烈的心,隨著人流涌出車站。第一眼的鄭州,在我的記憶里是灰黃色的,像一幅褪了色的年畫。空氣里彌漫著煤煙與塵土混合的氣息,寬闊的馬路兩旁,是枝葉闊大的法國(guó)梧桐,風(fēng)一過,便簌簌地響,落下些焦黃的、帶著斑點(diǎn)的葉子來(lái)。
我記得最清楚的,是那無(wú)處不在的建設(shè)的氣息。那時(shí)雖沒有“中部崛起”這般響亮的口號(hào),但那向上的、生長(zhǎng)的力量,卻是實(shí)實(shí)在在地夯在這片土地上的。到處都是腳手架,像巨人裸露的骨骼;打樁機(jī)的聲音,“咚—咚—咚”,沉重而緩慢,像一顆巨大而穩(wěn)健的心臟在搏動(dòng)。我的一個(gè)同窗,便是鄭州本地人,他有著一副中原漢子常見的身板,寬厚,結(jié)實(shí)。他帶我在城里轉(zhuǎn),指著那些新起的樓宇,言語(yǔ)間滿是自豪。有一回,過馬路時(shí),一輛卡車呼嘯著從身旁擦過,他下意識(shí)地用他那鋼筋似的手臂,將我往身后一攬。那股力量是溫和的,卻是不容置疑的,帶著這片土地所賦予的、一種天然的擔(dān)當(dāng)與可靠。那一攬,仿佛便將我與這座城,在剎那間拉近了。那手臂的力道,與那打樁機(jī)的夯聲,便在我年輕的心里疊印在一起,成了我對(duì)鄭州最初、也最牢固的印象。
如今,二十六年彈指而過。我走過許多地方,見過許多城市,鄭州的面目,在傳聞與新聞里,也早已煥然一新。它成了“國(guó)家中心城市”,成了“中原經(jīng)濟(jì)區(qū)”的核心,那“中部崛起”的浪潮,將它高高地托起,成了名副其實(shí)的前沿。我來(lái)時(shí)坐在車上,穿過鄭東新區(qū),但見高樓林立,造型奇崛,反射著天光云影,一派國(guó)際都會(huì)的氣象。那昔日的“鋼筋似的手臂”,如今已化作了“大玉米”那般秀挺而豐腴的線條,化作了高架橋上流暢蜿蜒的車河。這自然是極好的,是勃勃的生機(jī),是光明的希望。
然而人心總是古怪的,置身于這嶄新的、宏偉的圖景中,我卻偏偏想起那些舊的、細(xì)微的物事來(lái)了。我忽然很想再去看看德化街,看看二七塔。
第二天,我便真的去了。德化街是全然不認(rèn)得的老相識(shí)了。路面是光潔的石材,兩旁是琳瑯的、時(shí)尚的店鋪,衣著光鮮的男男女女,像彩色的溪流,在明凈的櫥窗前淌過。熱鬧是加倍的熱鬧了,繁華也是加倍的繁華了。我費(fèi)力地在記憶中搜尋,想找出一點(diǎn)當(dāng)年的痕跡。記得那時(shí),街兩旁多是些老式的百貨商店,門口掛著深藍(lán)色的布簾子,一掀開,便是一股混著糖果、布料和肥皂的氣味撲面而來(lái)。還有那賣烤紅薯的爐子,在寒冷的冬日里,冒著甜絲絲、暖烘烘的白氣。如今,這些都尋不見了。只有那座沉默的二七紀(jì)念塔,還屹立在原地,像一個(gè)穿著舊式服裝的忠厚長(zhǎng)者,略顯拘謹(jǐn)?shù)卣驹谝蝗盒鷩W的、追逐時(shí)髦的年輕人中間,帶著一種溫和的、寬容的神情,凝視著這日新月異的人間。
我在塔下站了許久。風(fēng)從塔身的飛檐間穿過,發(fā)出嗚嗚的聲響,像是歷史的嘆息,又像是對(duì)未來(lái)的叩問。這塔,是為了紀(jì)念一場(chǎng)著名的鐵路工人大罷工而建的。它本身就是一種“聲音”的象征,是爭(zhēng)取自由與光明的吶喊。而此刻,它被淹沒在了一片消費(fèi)的、娛樂的聲浪里。這變遷,究竟是失落,還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告慰呢?我說不清楚。
友人知我好古,便說:“你既念舊,我?guī)闳タ磦€(gè)真正舊的東西。”
我們便驅(qū)車往北,去了黃河邊上。正是枯水時(shí)節(jié),那被譽(yù)為“母親河”的黃河,顯露出她溫馴而甚至有些寂寥的一面。河水是濁黃的,緩緩地流著,岸邊的灘涂遼闊地伸展出去,上面生著一簇一簇的蘆葦,開著白茫茫的花。風(fēng)吹過時(shí),萬(wàn)頃蘆花便如浪一般起伏,發(fā)出一種蕭瑟的、干爽的聲響。遠(yuǎn)處,黃河大橋橫跨兩岸,如一道鋼鐵的長(zhǎng)虹。我們站在那里,誰(shuí)也不說話。這天地間仿佛只剩下三種東西:沉默的我們,流淌的河水,與搖曳的蘆花。
這景象,忽然讓我感到一種莫名的安寧。那城市的喧囂,那歷史的沉重,那未來(lái)的呼喚,仿佛都被這亙古的流水與飄散的蘆花滌蕩得淡了。我想,這黃河,她見過多少王朝的興替,多少城市的枯榮?在她面前,一切的崛起與沉寂,都不過是瞬間的漣漪罷了。然而,也正是這沉默的、渾厚的流淌,孕育了岸邊的一切,包括那座正在奮力雄起的城。她是所有的起點(diǎn),也是所有的歸宿。
從黃河邊回來(lái),天色已向晚。城里的燈火又一次亮了起來(lái),比昨夜所見,似乎更要璀璨些。我又想起了那“胭脂”。此刻,這萬(wàn)家燈火,這流光溢彩的車河,這不眠的街市,不正是今日鄭州所敷的胭脂么?它不再是羞澀的、隱秘的,而是豪邁的、自信的,大大方方地涂抹在城市的臉上,映照著中原的夜空。
而那從遠(yuǎn)方傳來(lái)的聲音,此刻我也仿佛聽真切了些。它不再是記憶里那孤零零的打樁聲,也不再是二七塔那帶有悲壯色彩的風(fēng)聲,更不是黃河那永恒的流淌聲。它是所有這些聲音的合鳴,是古老的管城之韻,是奮進(jìn)的鐵路之吼,是新時(shí)代的潮涌之音。它們交織在一起,沉雄而嘹亮。
今夜,我大約能看清鄭州的拂曉了吧。當(dāng)?shù)谝豢|光投射在那尊商鼎的雕塑上,投射在“大玉米”光潔的幕墻上,也投射在靜靜流淌的母親河上時(shí),那胭脂,想必會(huì)呈現(xiàn)出最動(dòng)人心魄的色彩。那色彩里,有土的沉厚,有血的熾熱,更有光的希望。
(使用“DeepSeek”改寫張廣智原創(chuàng)詩(shī)歌。圖片來(lái)自網(wǎng)絡(luò),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