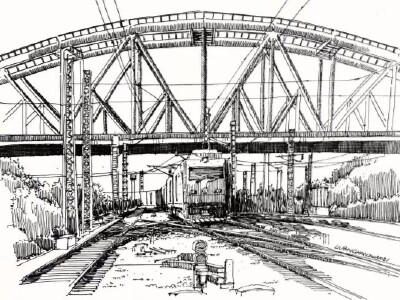我十幾歲時在濟南的郊區讀書,上放學路上要走過三五個村莊。何處車多路堵、坑多水深我都記得,騎車時需謹慎;何處坡緩草軟、人稀路展都難忘,行車如沖浪。被接連不斷的房屋加持的村中道路,如深巷,經此,常有犬吠,常有鵝鴨追逐。街邊閑聊的老人,我也似乎熟悉了他們的面龐和聲音。
幾十年后,我再到這里來,這里已是不斷擴張城市的一部分,高樓拔地而起,道路縱橫交
錯……村莊不見了,連村莊的名字都不見了。
我不知道搬進樓房的人們是否在意腳下還是不是自己的土地,但我知道桑梓遺塵不是文人獨有的情懷,故園鄉愁是人類共有的寄托。這座城市是當下中國的縮影。“拆遷”之后的大樓如雨后春筍般節節攀高,可否為鄉愁留一點兒空間?
有一天,我去一所新建的社區學校,剛好這是所村民安置區的學校。陪同的幾個干部是原來村子里走出的人,他們用手給我指原來村子的方向。村子已然沒有了痕跡,問起關于村子的掌故,他們如數家珍,懷念之情溢于言表。我忽然想到,學校可以為保留鄉愁做些工作,那樣可以一舉多得。
我設想:把環校的道路當作馬路,設若干車站,以村名命之,如張村站、王莊站,站點可以露天,也可棚蓋,棚則以舊村之瓦覆之。盡可能多地收集寄托了人們情感的物件,大的如馬槽、碑刻,小的如算盤、煙桿,煙火氣如灶臺、風箱,典雅如家譜、畫像,等等。東西少就置于站點,東西多則可沿路擺放。如有大片的空地可以打造村居景觀,師生共同設計,砌墻造物、鋪路架橋,研究用什么造型、什么材料能代表不同村落的共性特征,從繪圖、進料、施工系列展開。
這樣不僅保存了村居的物質記憶,而且有大量非物質遺產的傳承。
我想:可以在站點的圖標和聲音、文字介紹上下功夫,發揮學生的繪畫和文學天賦;可以將其作為課題,通過進行調研和訪問,提煉能代表村子的元素,從不同角度介紹村子的歷史;可以在站點辦畫展,辦內容不斷更新的畫展。聽健在的老人講村史、講家史、講掌故、講趣事,也可以將其錄制成視頻,既能夠隨機播放,又可以點擊選擇播放,在傾聽時產生“老吾老”的共情之心。
故事里的事是你的也是我的,故事發生地是你的鄉也是我的鄉。把失地的村莊搬進校園,通過故園窗口打開祖國傳統文化的視野,禮義廉恥在其中,溫良恭儉讓在其中,浩然之氣在其中,詩情畫意在其中。勤奮好學找到最近的榜樣,勤儉節約有身邊的例證。
這些工作,沒有學生的幫助是很難完成的,除了教師的幫助,更需要家長的幫助,家委會的價值就凸顯了。這件事情也會牽動眾多鄉親的心,收集的舊物可能就有他家的,采訪的老人可能就是他的父親,故事里的人物也許就是他的祖先,村史中的村是他的故園,家史中的家是他的記憶,校園為他保存了童年。一方校園凝結了周遭幾個村莊的淚點,“叫我如何不想她”?
這般思緒,在我的腦子里盤桓了很久,讓我沉醉其間。
為學生和原住民留住鄉愁的記憶,能是個小話題嗎?風箏飛得再遠,也有一根線牽著,斷線的風箏是空中的棄兒。中國人有深沉的故土之戀,少小離家,老大也想著一定要回來。在大時代的洪流中保留一點兒“小心思”,珍惜失地人的“大鄉情”,何止是為孩子們著想?不也是為我們這個民族著想的大事嗎?愛國之心源于愛鄉之情,老家被拆除了,只要先人的舊物在,只要先人的聲音在,只要先人的故事還能流傳,故園之情就沒有斷。
教育強調真實的情景,第二輪課改最大的亮點就是綜合實踐課程的開設。把失地的村莊搬進校園,有目標、有內容,能評價、可持續,自然可以稱作課程;活動需要調研、設計,需要動手、動腦,需要合作、創新,需要信息技術手段的支持,具有社會價值和現實意義,這不就是優質的綜合實踐課程資源嗎?
教育應該承擔起傳承文明、化育地方的功能。“家校社共育”中的“共”字,只有學生這個“被教育”群體是不夠的。把失地的村莊搬進校園,學生不僅是被教育者、活動的主力軍,而且是教育的最大受益者。家長除了要實現教育學生的目的,也在為自己的情懷而努力,既是育人又是育己。“家校社”中“社”是什么? “社”就是學校周邊曾經的村莊,是孩子、家長、村民共同的家園,家園為“社”,家園里的人也是“社”,“社”非虛也。
如此“多功能”的教育,何樂而不為?需要花錢嗎?錢多有錢多的設計,錢少有錢少的做法,貴在親手做,親在內中有感情。也不需要浩大工程、一蹴而就,貴在持續發展、不斷豐富,時間越久越顯難得。文物保護需要一個“搶”字,搶時間,搶空間。時過境遷,等到物不是、人已非的時候,再做已不可能。
與某校長談及,隱隱有“土氣”之憂。“土氣”之憂非個別人所有。現在,居住小區的名字動輒“盧浮宮”“巴黎鎮”;現在,學校的名字要么出自經典,要么“走向世界”,雅到極致,大到無邊,絕對不肯與一個“村”字相連。我想:學校如果辦得好,哪怕叫“回龍觀”也是好學校;辦得不好,就是叫個“二十八世紀”學校,也成不了教育的未來。把失地的村莊搬進校園,為未來留住鄉愁的記憶,何“土”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