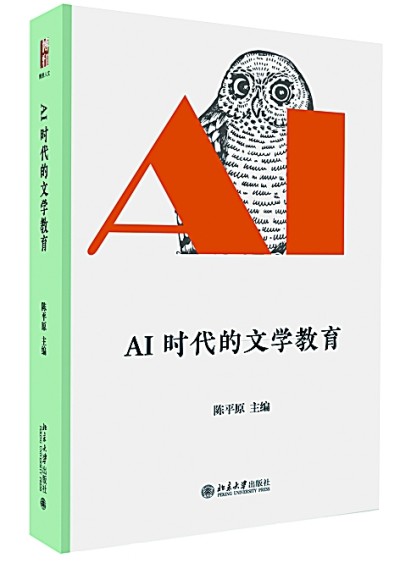
《AI時代的文學教育》陳平原 主編 北京大學出版社

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面對AI對人文學科帶來的巨大沖擊,北京大學陳平原教授召集學界同仁編撰《AI時代的文學教育》(入選11月光明書榜)一書,集中呈現了人文學界對顛覆性技術革命的敏銳回應。學者們在興奮、震驚與憂思中,將AI置于人文視野下審視,既考察其各個方向的影響力,又把它當作一面鏡子,從中折射出傳統人文學科歷久彌新的價值,以及一直存在的問題。
陳平原教授提出“與AI共舞”,這是一種主動、積極且介入的姿態。人文學者不愿被動地做技術的承受者,而要保持自身的節奏與步法,成為技術演進中的參與者和合作者。但是“共舞”也暗示著一種潛在的危險:舞伴的力量可能遠勝于你,你甚至可能被它完全引領。這正是陳平原教授編撰本書的主旨:“如何在接納AI這一神奇工具的同時,不被其控制與奴役。”這也是本書作者們共同面對的問題:既要避免陷入悲觀的技術決定論,又要警惕盲目樂觀的科技崇拜。在承認危機、適應變化的同時,步步為營地守護人之為人的價值與尊嚴。
以AI為鏡:重新審視人文之本
AI像是一個人類為自己創造的“他者”,我們在與這個不斷進化中的“他者”的互動和對比中,可以從一個前所未有的視角,來重新勘探人之為人的邊界,審視人文學科的核心價值。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也是一雙觀看人類自身價值和獨特性的眼睛。
與人類相比,AI最缺少的是什么?不少人都認為是情感。至少在目前AI還不能感知世界,無法真正體會人的喜怒哀樂。它的共情只是一種建立在文本特征之上的模擬。這一缺陷反而凸顯了人類情感體驗的寶貴。在此基礎上,多位學者不約而同地對具身性這個概念格外青睞。宋明煒教授認為,人類具有具身性和獨一無二的經驗,才有真正的生命,才有可能不被輕易操控。文學需要有呼吸,有此時此刻的具身性,才能生成不可思議的文學。邵燕君教授則重提控制論先驅諾伯特·維納的觀點,即人之不同于機器,就在于人會感覺疼痛、渴望愛、懂得審美,而這一切都根植于我們的肉身體驗之中。
AI讓我們更好地看見文學的具身性。哪怕是一個再小的場景,一句再短的詩,都不是通過拼湊語料庫得來的,而是來自我們身體的感覺,是我們生命體驗的整體。比如杜甫的《江南逢李龜年》寫的是一個與故人相逢的瞬間,但它包含了杜甫的一生,從開元盛世到安史之亂后,他年華老去、貧病交加的完整人生,以及個體與時代盛衰的關系,全都壓縮在這短短幾句詩里。如果想讓AI寫出這樣的詩,就得讓它作為一個人,完整地經歷所有的一切。這是不可能的。
還有一些學者嘗試用AI的眼睛回看自己所在的人文學科。劉復生教授提出一個很有啟發性的觀點:AI之所以能輕易模仿甚至超越大多數人的寫作,是因為它揭示了一個尷尬的事實:人類的文學創作與批評,在某種程度上早已“AI化”了。他認為,現代文學體制,尤其是新批評、結構主義等理論范式,早已在一片“作者已死”的聲音中,將文學創作和批評分解成一種技術性的語言操作程序,其底層邏輯與大語言模型并無二致。如今AI用自己強大的技術力量把去人類中心的趨勢推到人類無法和它競爭的地步。這樣說來,AI的沖擊就不只是一場必須抵御的危機,而是一個寶貴的機會,為早已陷入模式化困境的文學帶來了新生的機會,迫使人們去改造文化環境,追求真正有創造性的寫作和更人性的思維方式。
這里我們可以看見這本書中充滿張力的思想碰撞。一部分學者傾向于為人類做本質主義的辯護:人類擁有AI所不具備的情感、肉身、原創力,文學是守護這一人性內核的堡壘;另一部分學者則從歷史主義的角度提出,我們今天用來定義AI的一些方面,如模式化、非原創性、去情感化等,其實也不是AI的專利,而是人類自身在現代主義和網絡時代等特定歷史階段發展出的文化現象。AI究竟是一個映照出我們永恒人性的他者,還是一個我們自身在技術邏輯下創造出的鏡像?本書把這個問題嚴肅地擺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過程的意義:警惕認知的“捷徑”
人對自己的創造物總是抱有警惕,生怕它們會脫離自己的掌控,反過來對自己不利。AI是當今最有潛力的技術,人們對它的疑慮也自然而然地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強度。但人文學者們更擔心AI會不會導致人類核心能力的萎縮,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人類的思維能力。方維規教授在本書中就持這種觀點。他認為AI給人類帶來了極大的便利,但也可能會悄悄削弱我們的思維能力、判斷力和創造力,讓人在不知不覺間把決策權交給了技術。AI越聰明,我們越容易產生依賴感,甚至懶得去懷疑。我們得提防AI對人類創造力、自主性和思維能力的蠶食。這可不是杞人憂天,如果獲取信息就像打開自來水龍頭那樣方便,那些為尋求一個史料而出入圖書館、翻閱故紙堆的艱辛過程會不會逐漸消失?武新軍教授借用馮友蘭治史學需“求全、求真、求透、求精”的四個步驟來說明類似的問題。在AI時代,“求全”(收集史料)變得輕而易舉,而更為關鍵的“求真、求透、求精”反而變得愈發困難。面對AI瞬間推送的海量文獻,學者很容易失去深度消化咀嚼的耐心,從而喪失與史料熔鑄情感與生命體驗的機會,從“觸摸”歷史,變成了“點擊”歷史,最終失去歷史的在場感。
避難就易的傾向背后,還有更深層次的危機,那就是過程的失落。陳濟舟與蔣寅教授都提到了文學與藝術的精華在于審美體驗的過程,而不是結果。AI的運行邏輯是建立在大數據基礎上的概率計算,它會一瞬間從原因跳到最可能的結果,卻恰恰跳過了人腦在因果之間曲折、遲疑與靈光乍現的過程。在這種機制的規訓下,人類可能被逆向培養成高效的提示詞工程師,而不是提出真正問題的思考者。
AI也為人文學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胡曉明教授是著名的古典詩歌研究專家和詩人,從2019年起就關注AI與詩歌創作的碰撞。DeepSeek一問世,他就與之相互唱和,深度切磋,沉醉其中。他認為AI對于詩歌有很強的理解能力,能寫出語言優雅、形式精妙的古典格律詩歌,對各種詩風都駕輕就熟。更有意思的是,AI擁有與人類不一樣的觀察世界的視角和創作方式,這就給人類的詩人和詩歌研究者一個很好的與AI進行交流和切磋的機會,提高自己的創作和研究能力。
這些觀點交織成一幅復雜的圖景。對技術會損害人的認知能力的憂慮,其實并不新鮮。早在古希臘時期,蘇格拉底就擔心文字是一種認知的捷徑,會損害人天生的記憶能力,這也是把記憶看成一個不斷綿延的過程,而不是一勞永逸的結果。瓦爾特·本雅明哀嘆機械復制時代“靈韻”的消失,認為像電影這樣的新藝術形式,通過畫面的剪輯組合和快速變化的鏡頭角度,制造碎片化的震驚效果,使得觀眾不再是作品前凝神觀照的欣賞者,而是被動地接受一系列的視覺沖擊,這也像AI對人進行去過程化的塑造。針對現代教育中的效率至上、產出為王的功利主義傾向,學界也一直在呼吁捍衛“過程”價值。從這個意義來說,AI不是危機的始作俑者,而是危機的放大器與催化劑。它用一種更為強化和緊迫的方式,迫使人文學者面對那個一直在追問的問題:人文教育的價值究竟是什么?
“守”與“變”:人文教育的應對之道
我們該如何面對AI帶來的挑戰?學者們對于未來的人文教育進行了種種展望,想要在“守”與“變”之間尋求一種動態平衡。
首先要守住那些AI不能替代的人類核心能力。宋偉杰教授提倡對批判性AI素養的培養,他認為學生不僅要掌握AI工具的操作技能,更應該了解其生成機制,看清AI潛在的偏見與認知局限。方維規教授認為,未來的教育要把批判性思維和自主性放在首要位置,并化用笛卡爾的那句名言,提出“我懷疑,故我在”。懷疑精神正是打破新的信息繭房和戳穿AI“一本正經的胡說八道”的利器。
人的優勢在于想象、創造和共情,所以“真實體驗”顯得尤為重要,應當成為文學教育的重要目標之一。十多年前,陳平原教授就提出不能把文學課教成文學史知識課,要回到作品本身,培養學生的閱讀快感、審美趣味和思考能力。現在AI這面鏡子更照見文學活動的體驗性過程的重要性。基于同樣的思路,邵燕君教授提出要重新認識現實主義文學,把現實主義作品當作人類經驗的“體驗艙”和人性的“還魂器”,要在這個虛擬化、碎片化的時代為學生創造一個包含復雜人性與社會現實的空間。
人類知識和學術的進步本來就是過程化的。傳統的人文學者會用一輩子研究《紅樓夢》或者魯迅,通過漫長的積累形成知識體系。今天的學術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信息的檢索和提取。這種以結果為導向的研究,也伴隨著量化的評估體系,給人文學科的發展帶來了種種問題。AI的沖擊,可以說是把這些問題推到亟待改變的程度。
在學校里,AI最令人擔心的一個問題,就是可以幫人寫論文,讓傳統的考核方式失效。邵燕君教授建議把論文形式的考試改為口試。這個建議看似簡單,實則意味深長。這是把評估的重心從最終的考核結果,轉向了師生互動,包括思考過程、語言表達和臨場反應能力,這些都是AI替代不了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未來老師的角色也許會更像是學生的伴讀者和陪練者。這也賦予“言傳身教”這句老話全新的意義。AI讓我們更清楚地看到教育的關鍵不在于知識的灌輸,而在于師生關系的培養,更需要對話、具身和人的在場。
王賀教授提出要把“必要的保守”與“開放的人文學”結合起來,這是對各種應對之道貼切的總結。要以開放的心態,去探索AI作為工具帶來的可能性,主動調整課程設計與教學方法,以適應新的技術環境;與此同時,又要以一種近乎保守的姿態,去守護那些被技術邏輯沖擊的傳統價值,如深度閱讀、批判性思維、審美體驗和具身感知。當技術如脫韁野馬狂奔的時候,文學教育可以給人提供另一種節奏,讓人沉靜下來,看見內心的需求。
面對技術理性的不斷推進,《AI時代的文學教育》認為文學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培養出更完整、更豐富、更有感受力的人。在一個技術越來越多地代替人去思考和行動的時代,文學帶來創造、想象和獨特的具身體驗,這已經超越了審美的追求,成為捍衛人的精神生活和生命意義的行動。
我們在守住壁壘的同時,是否還可以去探索開拓一種更有建設性的人機關系的可能性?這就不僅需要問AI不能做什么,也要問在AI的幫忙下我們能做些什么以前想都沒想過的事。比如AI可以幫我們分析幾千本小說里的情感模式,可以追蹤一個文學意象在數百年里的變化軌跡,讓人文研究者能夠在更大的尺度上去做一些更加系統的研究。再向前走一步,在AI不能代替的人文活動中,我們是否可以打開一種新的范式,大膽地進入只有依靠人機協作才能到達的新的人文空間?
《AI時代的文學教育》沒有給出現成的答案。正如陳平原教授所說,它有價值的地方就是把人文學者當下困惑、迷茫、反思的東西都擺在了臺面上,讓大家知道這個問題的緊迫和復雜。要讓本書開啟的對話一直延續下去,我們就得帶著這些問題,投身到更廣闊的人文和技術的重組與融合的進程中,去探尋一條從防御到整合,再到創新的未來之路。這也是陳平原教授所說的“與AI共舞”的題中之義。
(作者:嚴鋒,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