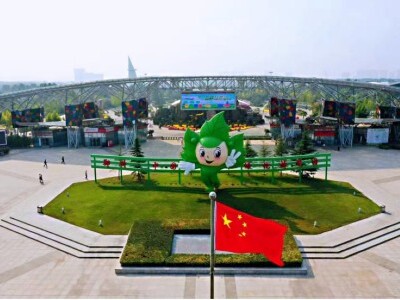風裹著細碎的白,掠過二七塔的尖頂,漫過玉米樓銀灰色的輪廓,把中原的冬意,輕輕鋪展。
金黃的法桐葉還沒褪盡秋的余溫,就被雪花溫柔覆蓋,枝椏間金白交錯,像一幅暈染的水彩。街道褪去了白日的喧囂,車轍碾過薄雪,留下淺淺的痕,街角的胡辣湯小店飄出熱氣,與空中的雪霧纏綿,暖了一城的清冷。
古城墻的垛口積了薄薄一層雪,青灰色的磚紋在雪色里愈發清晰,磚縫里還凝著幾分歷史的厚重,仿佛時光在這里放慢了腳步。城隍廟的飛檐掛著細碎的雪粒,朱紅的廊柱映著白,檐角的瑞獸裹著雪絨,添了幾分古雅的韻致。而玉米樓以流暢的螺旋線條立在金水河畔,圓潤的樓體裹著一層素白,恰似一支被雪吻過的玉簪,靜靜簪在城市的鬢角。玻璃幕墻反射著天光雪色,將河畔垂柳的疏影、遠處二七塔的尖頂,都揉進現代建筑的棱角里;環形窗欞間漏下的雪光,與城墻磚紋里的雪痕遙遙相望,古老與新潮在此刻相融,成了水墨長卷里最具煙火氣的一筆。
沒有北風的呼嘯,只有雪落的簌簌聲,漫過街巷,漫過城墻,漫過玉米樓的環形窗欞,漫過每一寸煙火人間。鄭州的雪,不是塞外的蒼茫,而是中原的溫潤,把市井的熱鬧暈染成一紙水墨——一筆是老城墻的青灰,一筆是玉米樓的銀白,一筆是法桐葉的金黃,一筆是歲月沉淀的暖。
雪還在落,落在塔尖,落在城墻,落在玉米樓的肩頭,落在熱騰騰的煙火氣里。此刻的鄭州,是被雪吻過的尋常巷陌,一磚一瓦,一檐一角,都是安然的詩意。
詩曰:雪夜懷思
朔雪敲窗夜色深,
燈前落筆意沉沉。
眼跳非關兇與吉,
肩頭自有重千斤。
良知枝上梅初綻,
暖粥爐邊火正溫。
一卷陽明消俗慮,
風輕月白好眠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