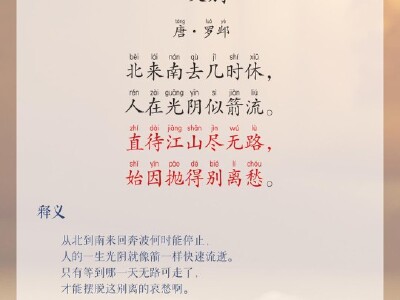當(dāng)我們談?wù)摲缸镄≌f,腦海中浮現(xiàn)的常是血腥的現(xiàn)場、縝密的推理、正邪的對(duì)抗。然而郭彤彤的《驗(yàn)明正身》以近乎叛逆的姿態(tài),將這一類型從感官刺激的泥沼中打撈出來,置于存在主義的光照之下。在這里,罪行不只是外部的暴力事件,而是內(nèi)化為一場詞語的起義、一次詩意的越界、一段精神的自戕。這部小說完成了對(duì)犯罪敘事的美學(xué)改造——用詩性的語言編織一張存在的蛛網(wǎng),讓那些不流血的傷口在詞語的顯微鏡下顯影,最終指向我們這個(gè)時(shí)代最隱秘的精神癌變。

郭彤彤,1971年出生于華陰馬王廟廂房。祖籍洛陽孟津西小梵東溝村,現(xiàn)長期居住在長安韋曲皇子坡畔摘星樓內(nèi),從事文學(xué)、口述史、藝術(shù)史撰述工作。
郭彤彤的筆觸犀利精準(zhǔn),卻又不失詩人的溫柔。他創(chuàng)造了一種奇特的敘事倫理:不審判,不解剖,而是“呈現(xiàn)”。小說中的罪,不只是法律意義上的違法,更是存在意義上的失重——當(dāng)一個(gè)人無法確認(rèn)“我是誰”,當(dāng)他在欲望的迷宮中丟失了返回自身的路徑,這種“存在的失竊”本身就是最根本的罪。而詩性語言,恰恰成為了探測這種無形之罪的唯一儀器。
一、血色修辭:暴力的語言煉金術(shù)
細(xì)讀文本,郭彤彤在《驗(yàn)明正身》中完成了一場驚心動(dòng)魄的語言實(shí)驗(yàn),他將犯罪敘事提升為一種詩學(xué)表達(dá)的實(shí)踐。這種詩學(xué)表達(dá)不是對(duì)暴力的簡單美化,而是通過語言的煉金術(shù),將暴力這一黑暗主題轉(zhuǎn)化為探究人類存在困境的哲學(xué)透鏡。當(dāng)周勃凝視同伙魏晉時(shí),看到的不是罪犯的猙獰,而是“清瘦而飄逸”的形象,仿佛“仙風(fēng)道骨也不過如此了”。這種將暴力行為詩意化的敘事策略,在小說中形成獨(dú)特的審美張力:一面是冰冷的犯罪事實(shí),一面是抒情詩般的語言表達(dá)。
小說開篇,在諾瑪雪塬的演出場景中,這種語言特質(zhì)就已初現(xiàn)端倪。唐姬跳著翻版的現(xiàn)代舞大師瑪莎·葛蘭姆的《深沉的樂曲》,在簡陋的舞臺(tái)上,“她的身體像漂浮在秋水上的葦草一樣”。郭彤彤用詩意的筆觸描繪暴力發(fā)生的場景,使得暴力不再是單純的社會(huì)失序現(xiàn)象,而成為一種具有美學(xué)意味的儀式。如周勃在行動(dòng)前的獨(dú)白:“我們身體里的力氣轉(zhuǎn)化成暴力,它像風(fēng)情萬種的少婦,以各種令人癡迷陶醉的動(dòng)作,引誘著我們綻放出絢麗多彩的獸性……”這種將暴力情欲化的修辭,揭示了暴力與人類潛意識(shí)深處欲望的隱秘聯(lián)系。
值得探究的是小說通過元敘事手法不斷解構(gòu)自身的真實(shí)性。敘述者直言不諱:“我把黑的說成白的,把白的說成黑的,都無關(guān)緊要”。這種自我指涉的敘事策略,使暴力從具體的社會(huì)問題升華為形而上的哲學(xué)命題。在長安城昏暗的街燈下,周勃的告白揭示了這個(gè)敘事世界的本質(zhì):“注定這些令我陶醉的日子都以過去時(shí)態(tài)出現(xiàn)在我的眼前,似乎與我根本無關(guān)”。作家郭彤彤以此暗示,在后現(xiàn)代語境中,連暴力都已蛻變?yōu)橐环N審美對(duì)象,這是對(duì)當(dāng)代社會(huì)暴力美學(xué)的深刻批判。
小說中反復(fù)出現(xiàn)的“白狼”意象。當(dāng)“魏晉看見那只白色的老狼猝然倒下的身姿”,這個(gè)意象不僅是暴力的象征,更是對(duì)暴力進(jìn)行詩學(xué)轉(zhuǎn)化的關(guān)鍵符號(hào)。白狼出現(xiàn)在諾瑪雪塬的回憶中,與唐姬的舞姿形成奇特的對(duì)應(yīng)關(guān)系,暗示著暴力與美之間微妙而危險(xiǎn)的聯(lián)系。郭彤彤通過這種詩學(xué)處理,使暴力敘事超越了簡單的道德評(píng)判,進(jìn)入了更深層的存在論域。
二、暗夜舞者:犯罪的美學(xué)儀式與存在困境
小說中的犯罪行為被賦予了詭異的儀式感,仿佛一場精心編排的現(xiàn)代舞劇。周勃、魏晉、劉邦三人用兒童面具遮蓋面容的場景,堪稱這種美學(xué)儀式的典范:“我們用每一件兒童面具遮蓋一次我們的臉,相互審視,直到我們雙方只能記住對(duì)方變化各異的臉,而忘卻了兒童面具后面的那張臉為止。”這個(gè)細(xì)節(jié)生動(dòng)展現(xiàn)了暴力行為如何將人異化為符號(hào),而面具之下的真實(shí)自我反而在暴力的美學(xué)儀式中逐漸消隱。
在諾瑪雪塬的回憶中,這種存在困境得到更深徹的展現(xiàn)。唐姬在簡陋舞臺(tái)上的舞姿與血色背景形成強(qiáng)烈反差,而周勃的反思則揭示了暴力的本質(zhì):“我知道是死路一條,但我們是兄弟!”這種對(duì)暴力行為的詩意詮釋,暴露出代人通過極端體驗(yàn)確證存在的荒誕嘗試。當(dāng)三人行走在黃昏的長安街頭時(shí),他們置身于“夕陽被街燈涂得一塌糊涂”的景象之中,成為他們精神世界的完美隱喻:在價(jià)值虛無的暗夜中,暴力成了最后的精神圖騰。
作家郭彤彤對(duì)犯罪過程的描寫極具儀式感和審美意味。在搶劫場景中,他寫道:“我們的腳步像貓一樣輕捷,我們的動(dòng)作像舞蹈一樣優(yōu)美。”將犯罪行為比作舞蹈,這種修辭策略不僅以詩性語言呈現(xiàn)了暴力,更重要的是揭示了現(xiàn)代人將暴力行為儀式化的心理機(jī)制。在另一起案件中,周勃描述道:“刀鋒劃過夜空的聲音像小提琴的弓弦劃過琴弦”,這種將暴力聲音藝術(shù)化的處理,使得犯罪行為具有了一種詭異的美學(xué)品質(zhì)。
小說中對(duì)長安城的描寫也充滿了這種儀式感。當(dāng)夜幕降臨,“長安的燈火像祭祀的燭火一樣閃爍”,城市本身就成了一個(gè)巨大的儀式場所。在這個(gè)場所中,暴力行為不再是簡單的犯罪,而是一種具有象征意義的儀式。郭彤彤通過這種敘事策略,揭示了現(xiàn)代都市生活中暴力儀式的普遍性和隱蔽性。
三、破碎的鏡像:暴力敘事中的倫理迷宮
結(jié)合作品不難看出,郭彤彤通過復(fù)雜的敘事結(jié)構(gòu),構(gòu)建了一個(gè)充滿張力的倫理迷宮。周勃在面對(duì)魏晉關(guān)于共同犯罪的提議時(shí),陷入深刻的存在主義焦慮:“魏晉看上的女人,我再插一杠子,把呼倫貝爾大草原給魏晉戴頭頂上?我也太沒人味了!”這種自我詰問展現(xiàn)了暴力對(duì)主體性的侵蝕,也揭示了后現(xiàn)代倫理的困境。
小說中“白狼”意象的反復(fù)出現(xiàn),強(qiáng)化了這種倫理困境的象征意義。當(dāng)“魏晉看見那只白色的老狼猝然倒下的身姿”,這個(gè)意象既象征著暴力本身的野性,也暗示著超越暴力的可能性。在長安城北城門樓的黃昏時(shí)分,周勃的獨(dú)白將這種倫理困境推至頂點(diǎn):“我看不見我的臉/只聽見我的聲音/我的手摸摸我的臉/卻摸不著我的聲音……”這種自我異化的體驗(yàn),正是現(xiàn)代人道德迷失的生動(dòng)寫照。
作家小說對(duì)于女性角色的倫理困境的描寫很出色。唐姬這個(gè)角色處于多個(gè)男性暴力的交匯點(diǎn)上,她的身體成為暴力和欲望交織的場所。當(dāng)周勃描述唐姬時(shí),他寫道:“她的眼神像受傷的母鹿,卻又帶著某種令人不安的誘惑。”這種描寫揭示了女性在暴力敘事中的復(fù)雜位置——既是受害者,又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暴力的共謀。作者通過這種復(fù)雜的角色塑造,打破了非黑即白的善惡二分法,展現(xiàn)了暴力倫理的復(fù)雜性。
在劉邦這個(gè)角色身上,郭彤彤展現(xiàn)出了暴力如何扭曲人際關(guān)系的藝術(shù)表達(dá)。劉邦對(duì)周勃說:“我們是兄弟,不值!”這句話表面上是強(qiáng)調(diào)兄弟情誼,實(shí)則暴露了暴力環(huán)境下人際關(guān)系的異化。在暴力的陰影下,連最親密的關(guān)系也變得工具化和扭曲。郭彤彤通過這些人物關(guān)系的描寫,打造出一個(gè)錯(cuò)綜復(fù)雜的倫理迷宮,在這個(gè)迷宮中,傳統(tǒng)的道德準(zhǔn)則失去了解釋力,而新的倫理秩序又尚未建立。
四、長安寓言:都市空間的暴力詩學(xué)
長安城在小說中不僅是故事背景,更是具有獨(dú)立生命的敘事主體。郭彤彤筆下的長安是一個(gè)充滿張力的符號(hào)空間:“長安街市的盡頭處虛構(gòu)成一幅杰克遜·波洛克的‘秘密的守護(hù)者’,色調(diào)沉郁、雜亂且迷離。”這個(gè)現(xiàn)代主義繪畫的比喻,精準(zhǔn)捕捉了都市空間的異化本質(zhì),暗示了暴力與都市生活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
在小說結(jié)尾,當(dāng)周勃感嘆“發(fā)絲(雪白的)在魏晉的注視下飄然墜落”時(shí),這個(gè)意象既是個(gè)體命運(yùn)的縮影,也是整個(gè)時(shí)代的隱喻。郭彤彤通過長安這個(gè)微觀宇宙,展現(xiàn)了一個(gè)更大的寓言:在物質(zhì)豐裕而精神貧瘠的現(xiàn)代社會(huì)中,暴力如何從具體的社會(huì)問題蛻變?yōu)榇嬖诘睦Ь场.?dāng)紅色的血“覆蓋了道德世界里的一切”,這個(gè)強(qiáng)烈的意象是一個(gè)故事的終結(jié),更開啟了對(duì)整個(gè)時(shí)代精神狀況的著重反思。
對(duì)長安都市空間的描寫極具象征意義,作家在小說中寫道:“長安的街道像血管一樣蜿蜒,而暴力就像血液一樣在這些血管中流動(dòng)。”這個(gè)比喻揭示了暴力與都市空間難以割裂的共生關(guān)系。在另一個(gè)場景中,他描述道:“高樓大廈的玻璃幕墻像刀鋒一樣反射著月光”,現(xiàn)代建筑本身就成為了暴力的隱喻。通過這些空間意象,郭彤彤展現(xiàn)了暴力如何滲透到都市生活的每一個(gè)角落。
值得注意的是小說中對(duì)長安地下世界的描寫,周勃描述道:“地下通道像子宮一樣黑暗而溫暖,孕育著各種形式的暴力。”這種描寫將暴力與生命本能聯(lián)系起來,隱喻暴力在人類存在中具有根源性。在描寫黑市交易場景時(shí),郭彤彤寫道:“交易的過程像宗教儀式一樣莊嚴(yán)肅穆”,揭示了暴力經(jīng)濟(jì)中的儀式化和異化特征。
《驗(yàn)明正身》之可貴,在于作家既未簡單譴責(zé)也未美化暴力,而是以詩性的語言和復(fù)雜的敘事結(jié)構(gòu),將暴力轉(zhuǎn)化為探究現(xiàn)代人生存困境的多棱鏡。他成功地在類型文學(xué)與純文學(xué)之間架起了橋梁,既吸收了犯罪小說的敘事張力和大眾吸引力,又注入了嚴(yán)肅文學(xué)的哲學(xué)深度和詩性語言藝術(shù)。這種創(chuàng)作嘗試,首先體現(xiàn)在他對(duì)“可讀性”的重新定義上。傳統(tǒng)觀念中,可讀性往往意味著情節(jié)的緊湊、語言的直白、意義的透明。但郭彤彤證明,真正的可讀性可以源自思想的挑戰(zhàn)、語言的微妙、意義的豐富層次。他的小說像一件精美巧妙的藝術(shù)編織,讀者可以滿足于表層的懸疑故事,也可順著敘事脈絡(luò)深入其紋理,探索其中存在主義的迷宮、社會(huì)批判的鋒芒和語言實(shí)驗(yàn)的匠心。
長安作為作家的故鄉(xiāng),也作為小說中的“故鄉(xiāng)”,在虛與實(shí)的交替中,引出了中國文學(xué)一直在尋找表達(dá)現(xiàn)代人異化、疏離、焦慮的方式。郭彤彤找到了一種既根植于本土經(jīng)驗(yàn)(長安的地域性、轉(zhuǎn)型期中國的特殊陣痛),又連接人類普遍境遇的表達(dá)方式。他的人物是具體的、地方的,但他們的困境是普遍的、永恒的。讓我們看到,無論是長安的月光還是巴黎的月光,照亮的或許是同一種鄉(xiāng)愁——不是地理的鄉(xiāng)愁,而是存在的鄉(xiāng)愁。
作者簡介:

張蕾,陜西省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重點(diǎn)研究基地“陜西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員;陜西省漢語國際教育協(xié)會(huì)理事;西安文理學(xué)院校聘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