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當下對“作家”身份的想象、稱謂的認定,已從神壇走向日常。這種祛魅過程,其實是社會對創作認知的一種成熟。
身份、地位、名聲、生活方式,傳統敘事中往往與作家緊密綁定,仿佛成為作家就自動獲得了某種光環。今天越來越多人意識到,寫作首先是一種內在的、近乎本能的沖動,是個人與語言、與表達之間建立的私密關系。它不是勛章,而是工具;不是目的地,而是旅程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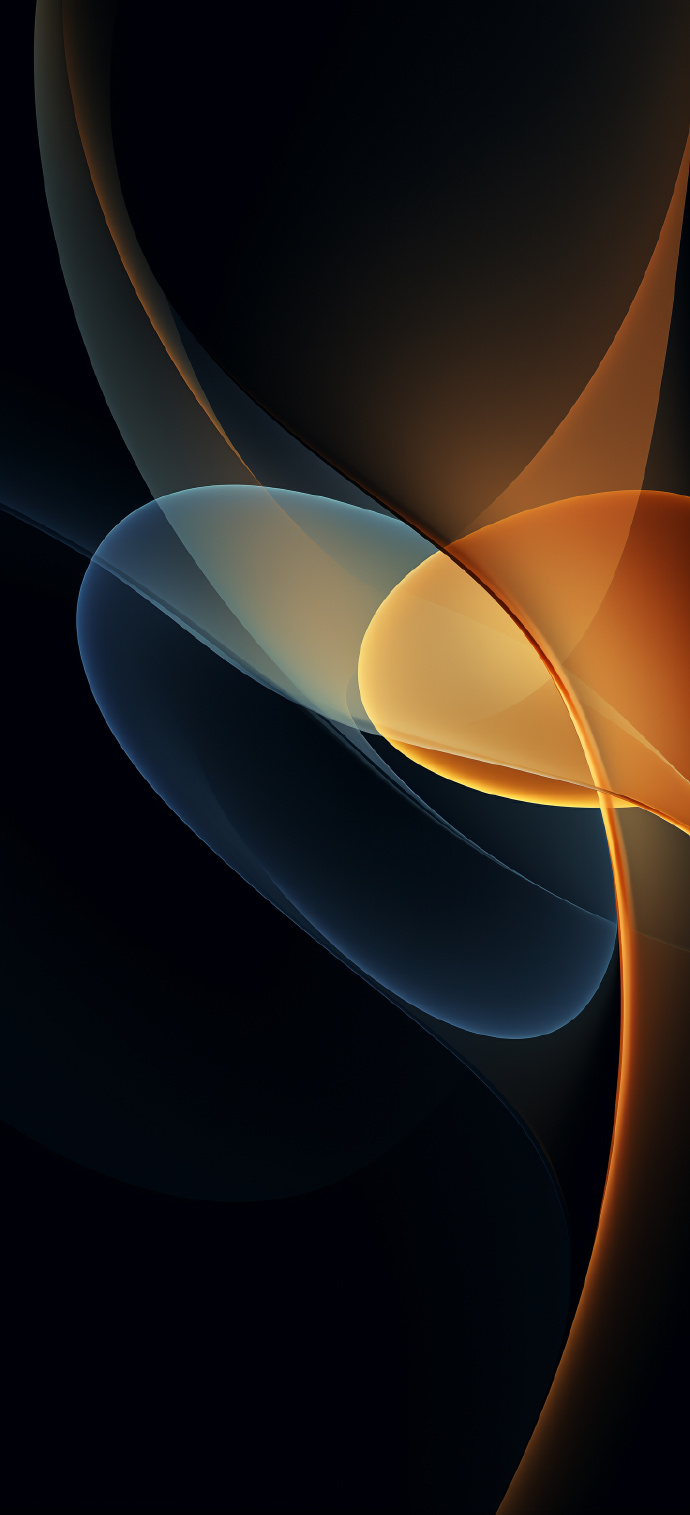
不過祛魅之后,寫作可能回歸到更本質的價值:
熱愛本身就是目的。當寫作剝離了外在標簽,那種“自帶的熱愛”反而更純粹。它不再需要被“作家”這個頭銜證明,就像鳥兒歌唱不需要被稱為歌唱家。這種狀態下,創作可能更自由,更貼近本心。
寫作重新與“普通人”的生活融合。許多人在日常工作、育兒、旅行之余寫作,寫作不再是特殊職業,而是像烹飪、園藝、運動一樣的生活方式選項。它塑造生活,但不一定顛覆生活。
“作家”標簽的流動性增強。今天,一個人可以同時是程序員、母親、徒步愛好者,也是寫作者。身份是流動的,寫作只是自我表達的其中一個出口。這打破了“作家必須全身心奉獻”的舊神話。
但寫作的古老魔法依然存在。即便祛魅,文字仍保留著某種不可替代的力量:整理思緒、對抗遺忘、連接他人、創造意義。這些內在價值,不依賴外部承認而存在。或許,祛魅后的寫作反而更接近本質:它不再是一個需要被認證的身份,而是一種可選擇的存在方式——用語言凝視生活,在書寫中確認自己的輪廓。當寫作不再承擔“定義我是誰”的重擔,反而能更輕盈、更持久地陪伴那些真正需要寫作的人。
最終,寫作可以是職業,也可以是修習;可以是利劍,也可以是容器。重要的是,它回到了書寫者手中,成為他們可以自由使用的工具之一,而非束縛他們的冠冕。
